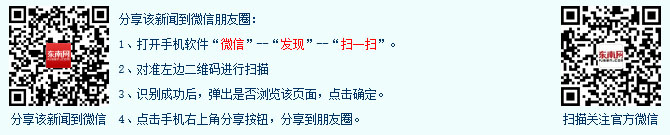“陸家山水”武夷情 葉禮璇/文 面對水清如玉的九曲、無勢不奇的山峰,國畫山水大師陸儼少激情難抑,吟詩道: “三三六六畫堪詩, 臨水登山事事嘉。 旬日武夷知不足, 不妨此地老煙霞。” “煙霞”者,“云氣”也。武夷山的云氣一入陸先生之畫面,如挾風雷的動勢頓時從宣紙上騰起,一破傳統(tǒng)山水畫之寂靜、呆滯…… 確實,陸先生視武夷山水為知音者,這不難理解,自1956年起,四訪武夷。第四次的訪游,時逾半月之久。次數(shù)之多,時間之久,當代美術(shù)名家圈中陸先生當為首位。 1956年9月,作為上海畫院中的佼佼者,陸先生被選為嘉定區(qū)人大代表,有更多機會飽覽祖國山河,他選擇了南下的線路,訪游革命圣地井岡山后,抵達武夷山。 時逢雨竭初晴,山嵐彌漫,茫茫云海中的群峰忽隱忽現(xiàn)于波濤 萬頃之中…… 九曲水一碧如染,如玉帶盤繞山中。山回溪折,折復繞山…… 充溢靈性的武夷山水——留在陸先生的創(chuàng)稿之中,或鉛筆或鋼筆勾勒…… 此時的陸先生已揉合南北二宗,初創(chuàng)出縝密娟秀之畫風,靈氣顯露,變幻無方。 我以為是原生態(tài)的武夷山水為畫壇大家的藝術(shù)生命注入了蓬勃生機。似無痕,然留跡。 回滬之后,陸先生為了讓傳統(tǒng)山水流傳有緒,不絕如縷,有了編寫一本關(guān)于山水畫技法的書的設想。 頭上還戴著“右派”帽子的陸先生白日在畫院打雜工,夜晚下班,晚飯后在馬路邊路燈下,俯身小小方凳,從事寫作,時常寫到夜深入靜…… 飽經(jīng)風霜而堅韌頑強,令筆者遙想起屹立千壁上的天游峰雄姿……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脫去“右派”帽子的陸先生及老伴偕劉旦宅夫婦一同到名山大川寫生,于是有了陸先生的二游武夷。 1973年后,中美開始接觸,周總理為了美化環(huán)境,迎接四方友賓,調(diào)一批畫家到北京,為涉外酒店、賓館作畫。 文藝界松動的信號發(fā)出之后,陸先生調(diào)入杭州的浙江美術(shù)學院。雖然未拿到正式員工的指標,但一年的兩個假期還是讓他欣慰。 1975年,陸先生利用暑假,第三次南下,直奔闊別十余載的武夷山。 上回尚在中年,此次已是老者。然而,未改容顏的依舊是那山那水……素樸一如往日的武夷山張開大臂迎抱畫壇的這位虔誠藝術(shù)之子。 畫家忘卻了身負之榮辱,全身心地投入到武夷山水的創(chuàng)作之中,“留白”之風格得以發(fā)揮,宣紙上林木滿山,云氣繚繞,流水潺潺,留白處變化多姿,顯現(xiàn)出了裝飾美,“陸家山水”的美學價值初現(xiàn)于此。 陸先生1975年創(chuàng)作的山水冊頁之四為《武夷九曲圖》,題款簡約,僅有“武夷九曲閩游紀勝”八字。“九曲”被畫家安排至畫作左側(cè)之一隅,而山峰則占據(jù)了絕大空間,山之色也并非“黑塊”,而是有青綠夾雜其間。筆者推測,其時,變革畫風之念頭正在畫家心中萌發(fā)…… 1978年5月創(chuàng)作的畫軸《福建林區(qū)圖》則還是保留畫家原有的風格之作,溪流有放排情景,激流中可見排工搏擊水浪之英姿…… 冰河解凍,春回大地。隨著國家民族命運的巨大轉(zhuǎn)折,陸先生的人生漸入佳境: 1979年11月,中國美術(shù)家協(xié)會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陸儼少當選為協(xié)會理事。 1980年,陸儼少晉升為浙江美術(shù)學院教授。其后當選為浙江畫院院長。 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 1984年秋月,陸先生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訪游武夷山。年過古稀的先生盡管身份、地位非當年可比,但老畫家一如往日的淳樸、敦厚、謙和。 其時,住在武夷賓館的陸先生接到應約到北京為人民大會堂繪大型國畫的電話,因而多留住了十余日。 多數(shù)時間,上午外出對景寫生,午睡后作畫,每每將畫作夾掛于室內(nèi)的鐵絲上,隨日增多,蔚為觀止。 對陪同前來的友人,陸先生贈畫表達謝意。畫面的“江南早梅”,似乎不合當年的時令,然而拜讀先生的生平有關(guān)文章、資料,使可得到合乎情理的答案。 陸先生的國畫創(chuàng)作,以冊頁、手卷最為精堪。創(chuàng)作的《愛新就新冊》便是其中之代表作。其之三為《閩嶠林區(qū)圖》題款為: “閩嶠林區(qū),予至福建,見其植被之厚而嘆,林木之不可勝用也。當公路蜿蜒以進,依山傍澗,蔥籠郁茂,林海廣袤,數(shù)十里路無隙”。 “嶠”在詞典中解釋為“山道”,是書面語,僅這一字可見大師傳統(tǒng)文字功力不一般。 題款的結(jié)尾處為:“丙子儼少并記”一查年歷表,筆者大吃一驚,靠近的,“丙子”年不是“1936年”即是“1996年”,前者不靠譜,而后者更大錯矣,陸先生1993年就逝世了。顯然老畫家記時有誤,名家也是人,犯錯難免。如寫“甲子”即1984年訪游武夷之后創(chuàng)作倒是有可能的。有一畫冊中言,這是先生1975年的作品,這也是不對的。 八十年代初,陸先生已形成自家畫風,也就是我們常見的“勾云”、“留白”、“黑塊”的“陸家山水”,并有程式化傾向。 陸先生是有思想的人,他不想重復自己,于是心中醞釀著思變。離開武夷山,完成北京作畫任務,回到杭州時他開始行動:他托人買來歐洲名家畫集,同時買來外國的顏料,學習趙無級抽象油畫章法形式。 當然他不會簡單地跟趙無極走,而是按吳冠中說的“穿著大師的拖鞋走一走,然后把拖鞋扔了,在穿和脫的過程中找到自己。”的辦法去嘗試。 由于陸先生傳統(tǒng)功力厚,加之思考能力超強,觸類旁通,不久,便創(chuàng)作出了嶄新的風格。 《閩嶠林區(qū)圖》中,畫家保留了“勾云”、“留白”、“黑塊”不見了,代之以“蒼綠”,武夷山的大王峰巍然挺立,頗有氣勢。這幅畫作,無論從構(gòu)圖、用筆,還是色彩與舊作大不同。筆者斗膽推測,此畫正是陸先生革新畫風時期的探索之作,至少留有變革的足跡。 在后來的《自敘》中,陸先生是如此回顧的: “翌晨即去武夷,住山中半月,暢游九曲之勝,上登天游,磴道依石壁而上,極為險峻。近望接筍峰,壁立千仞,徑路斗絕,石級幾不容足,奇險恐不在華岳之下。我常恨武夷不入畫,自登天游,奇石嵌空,危峰回合,盡多粉本,而向之觀看電視,參閱照片,皆不足據(jù)。”登天游俯看武夷山水勝境,大美如畫,老畫家創(chuàng)作激情迸發(fā)而出。 詩吟武夷事事嘉,醉寫山水卷卷新。陸儼少先生的武夷之行令人時時回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