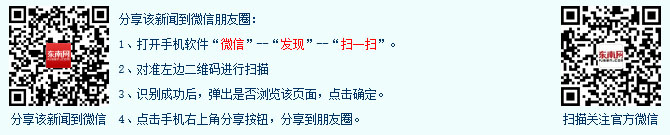|
(二)、陸九淵之心的來(lái)源 陸九淵的心學(xué)也來(lái)源于北方理學(xué)諸子,但其源頭直承《大學(xué)》“正心”、孟子“四端”之心。 儒家重要經(jīng)典《大學(xué)》,把心放在重要的位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guó)。欲治其國(guó)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chéng)其意。……誠(chéng)意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guó)治,國(guó)治而后天下平。”“正心”是八目中的一條,強(qiáng)調(diào)要從個(gè)體開(kāi)始,一步一步向外邁進(jìn),最終實(shí)現(xiàn)天下大同。可見(jiàn),《大學(xué)》為陸九淵心學(xué)思想提供了豐富的滋養(yǎng)。孟子的仁愛(ài)思想也為陸九淵心學(xué)提供了養(yǎng)料。孟子說(shuō):“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yùn)之掌上。”[24](《孟子?公孫丑上》) 孟子的“四端”更為陸九淵的心學(xué)提供具體的參照。他說(shuō):“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25](同上)此即人之本心。“四端”表現(xiàn)人的四種處世態(tài)度或情感,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以此與仁、義、禮、智相對(duì)應(yīng)。“無(wú)惻隱之心,非人也;無(wú)羞惡之心,非人也;無(wú)辭讓之心,非人也;無(wú)是非之心,非人也”。 [26](同上)可見(jiàn),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判別人之所以為人的依據(jù)。沒(méi)有“四端”之心,就沒(méi)有仁、義、禮、智的外在表現(xiàn),就無(wú)法成為人。如何實(shí)現(xiàn)物我觀照,孟子提出的辦法是:“萬(wàn)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chéng),樂(lè)莫大焉。”[27](《孟子?盡心上》)漢儒趙岐注“物,事也;我,身也”。意思是說(shuō),世界上萬(wàn)事萬(wàn)物之理由天賦予了我,而我也完全具備了這種應(yīng)萬(wàn)物之理的性分。 程顥、程頤的心論對(duì)陸九淵也有重要的影響。程顥認(rèn)為“良知良能是本心”。 [28](《宋元學(xué)案》卷十二)二程提出:“然學(xué)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以求至。”[29](《二程文集》卷八)這里強(qiáng)調(diào)的是心的作用,治學(xué)的方法是先要明白學(xué)的目的,才能有進(jìn)取的方向。程頤更以小見(jiàn)大,以微見(jiàn)著,提出“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30] (《宋元學(xué)案》卷十五)可見(jiàn),二程把心視為通乎物理的路徑,強(qiáng)調(diào)要“道合內(nèi)外,體萬(wàn)物”, [31](同上)才能萬(wàn)物畢照。為此,二程提出要讀書(shū)求理:“人之蘊(yùn)蓄,由學(xué)而大,在多聞前古人圣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shí)而得之,以蓄成其德。”[32](《程氏易傳?大蓄傳》) 陸九淵之心與程顥之學(xué)有內(nèi)在的聯(lián)系。程顥主靜,窮理方法上偏重于“正心誠(chéng)意”;程頤主敬,窮理方法上偏重于格物致知。黃百家對(duì)陸九淵之學(xué)作出分析:“程門(mén)自謝上蔡以后,王信伯、林竹軒、張無(wú)垢至于林艾軒,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傳亦最廣”。[33] (《宋元學(xué)案》卷五十八)可見(jiàn),朱熹更多的是傳承程頤之學(xué),而陸九淵更多的是傳承程顥之學(xué)。 二程之后,心學(xué)的代表人物是包括陸九淵在內(nèi)的江西三陸氏。史載:“三陸子之學(xué),梭山啟之,復(fù)齋昌之,象山成之。”[34](同上,卷五十七)梭山、復(fù)齋、象山是同一學(xué)派人物,史稱(chēng)“三陸子”。陸九韶,字子美,撫州金溪人,因“學(xué)問(wèn)淵粹,隱居不仕,與學(xué)者講學(xué)梭山” [35](同上),人稱(chēng)“梭山先生”。陸九齡,字子壽,金溪?dú)w政(今江西省金溪縣陸坊鄉(xiāng))人,陸九淵之兄,人稱(chēng)“復(fù)齋先生”。陸九淵,字子靜,號(hào)象山。因書(shū)齋名“存”,世稱(chēng)“存齋先生”。因?yàn)樾膶W(xué)集成于陸九淵,其學(xué)亦稱(chēng)“象山學(xué)派”。 三陸子的學(xué)術(shù)一脈相承,都主張由內(nèi)外求的觀點(diǎn),強(qiáng)調(diào)要發(fā)明本心。陸九韶主張治學(xué)以切于日用為要,即“身體力行,晝之言行,夜必書(shū)之”。 [36](《宋史》卷四百三十四)也就是強(qiáng)調(diào)以心應(yīng)物而行之于日用最為緊要。陸九齡也強(qiáng)調(diào)要用心感應(yīng)外界事物,如此才能切己之行。他說(shuō):“身體心驗(yàn),使吾身心與圣賢之言相應(yīng),擇其最切己者,勤而行之。”[37](《宋元學(xué)案》卷五十七)陸九淵不僅繼承這種觀點(diǎn),而且對(duì)心作了概括和哲學(xué)性的發(fā)揮,認(rèn)為“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dāng)歸一,精義無(wú)二,此心此理實(shí)不容有二。”[38](《陸九淵集》卷一)“人心至靈,至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39](《宋元學(xué)案》卷五十七)陸九淵之所以強(qiáng)調(diào)心,是因?yàn)槿诵闹领`,因?yàn)橹领`才會(huì)至理至明,把住了心就把住了理。 他強(qiáng)調(diào)“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 [40](《陸九淵集》卷十一)在陸九淵看來(lái),物在我心,心外無(wú)物。只有將客觀之物納入我心,此物才存在。他斷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來(lái)今,概莫能外”。 [41](《陸九淵年譜》)所以他從宇宙二字得出一個(gè)啟發(fā)“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42](《陸九淵集》卷二十二) 從上述看,朱熹以“理”為萬(wàn)物的本原,是宋代理學(xué)中的“格物派”;陸九淵則認(rèn)為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是理學(xué)中的“格心派”。由于二人觀點(diǎn)不同,形成宋代理學(xué)中最大的兩個(gè)門(mén)派,以致“兩家門(mén)人,遂以成隙”。[43] (《宋元學(xué)案》卷五十七)即以朱子為代表的稱(chēng)理學(xué)派,以陸九淵為代表的稱(chēng)心學(xué)派,導(dǎo)致繼春秋百家爭(zhēng)鳴以來(lái)又一次學(xué)術(shù)史上的爭(zhēng)辯——鵝湖之辯。 鵝湖之辯的焦點(diǎn)是治學(xué)方法。朱熹的觀點(diǎn)是外物求理,從圣賢書(shū)中體驗(yàn)天理,強(qiáng)調(diào)讀書(shū)講學(xué)的重要性;陸九淵則強(qiáng)調(diào)要不必讀書(shū)外求,只要發(fā)明“本心”即可成圣成賢。他甚至放言“六經(jīng)注我,我注六經(jīng)”、“學(xué)茍知本,六經(jīng)皆我注腳”。[44] (《陸九淵集》三十四)所以朱熹認(rèn)為陸九淵教人之法太簡(jiǎn),而陸九淵則認(rèn)為朱熹教人之法支離。 鵝湖之辯,沒(méi)有辯出真知。朱熹認(rèn)為:“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在盡廢講學(xué),而專(zhuān)務(wù)踐履。于踐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旨。要其操持謹(jǐn)質(zhì),表里不二,實(shí)有以過(guò)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guò),規(guī)模窄狹,不得取人之善,將流于異學(xué)而不自知耳。”[45](《宋元學(xué)案》卷五十七)可見(jiàn),朱陸之學(xué)是理學(xué)系統(tǒng)中的“殊途”,黃百家稱(chēng)贊他們“豈惟不知象山有克己之勇,亦不知紫陽(yáng)有服善之誠(chéng)”。 [46](同上)又說(shuō):“(陸九淵)從踐履操持立腳,恐不得指為大病。但盡廢講學(xué),自信太過(guò),正是踐履操持一累耳。(朱熹)若使純事講學(xué),而于踐履操持不甚得力,同一偏勝,較之其病,孰大孰小乎?”[47](同上)黃百家認(rèn)為朱陸二人各有所偏,陸氏偏重日用操持,是其大病;朱氏純事講學(xué)而日用不得力,也是一大弊端,此評(píng)價(jià)實(shí)為中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