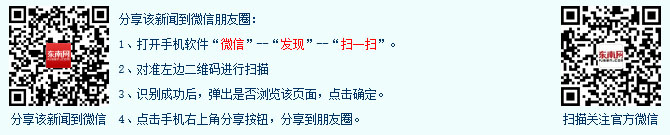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論語集注》卷二) 仁義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厘之差,千里之繆。(《孟子集注》卷一) 朱子認為,所謂“義”,就是符合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則的東西和道理,也即天理。所謂“利”,就是人訴求于自然、社會、他人的各種欲望,也即人欲。一事當前,如果我們能循著天理去做,那么,利之所歸是自然的。反之,如果我們一味地追求人欲,那么,“利”不但得不到,“害”也緊隨而來了。 在朱子看來,“義”和“利”是統一的,“義”里包含著“利”,“利”是“義”的必然結果。但是反過來,“利”卻不一定都包含著“義”。所以,朱子并不是反對“利”,他只是強調,要以“義”來統御“利”,要通過正確的目的、途徑、手段、方法(宜)去取得“利”。 同時,朱子也不是禁欲主義者,他認為人的欲望是與生俱來的,合理的欲望也就是天理。只有欲望過了度,才是“人欲”。 世間喻于義者則為君子,喻于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于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悮用其心矣。(《文集》卷二九《與楊子直書》) 這是朱子晚年給一位叫楊方的朋友寫信時特意提出的一段話。在朱子的時代,功利主義哲學十分盛行,而有一些學者不但不堅持正確的“義利之辨”,反而想要調和二者,為功利主義尋找借口。所謂功利主義,就是只講結果而不論動機和過程,只追求利益而不顧及道義。朱子和這種混同義利,甚至“以利代義”的理論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明確指出,孔子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正是把義利之別看作區分君子、小人的標準。朱子說,現在有人試圖模糊“義”“利”之間的界限,費盡了心機,最后既做不成君子,小人也做得偷偷摸摸,無疑是把心思用錯了地方。 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文集》卷一三《垂拱奏札二》) 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文集》卷七一《偶讀漫記》)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于害者。(《語類》卷一三) 世界上的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害,有所得必有所失。一事當前,不能只看到利害關系,而不顧是否合理、合法、合規。做事如果只考慮利害得失,其結果沒有不陷于禍害的。 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語類》卷九六) 《易傳·文言傳》里有一句話說,“利”,就是“義”得到了應該的、合理的、正確的、恰到好處的安排。可見,“義”里邊本來就包含著“利”。 朱子在《論語或問》里引用胡寅的話:“然自利為之,則反致不奪不厭之害;自義為之,則蒙就義之利而遠于利之害矣。”也就是說,你如果從“利”字著手,那就會招致搶不到手不滿足所帶來的禍端;如果從“義”字出發,那就會享有由義得利的好處而遠離利的害處。所以朱子認為,得“利”,講求的正是與“義”的統一(和),而萬事萬物,得到了應該的、合理的、正確的、恰到好處的(宜)就是得“利”。 圣賢做事,只說個“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事只如此做,何嘗先要安排紐捏,須要著些權變機械方喚做做事?又況自家一布衣,天下事那里便教自家做?知他臨事做出時如何?卻無故平日將此心去紐捏揣摩,先弄壞了。(《語類》卷七三)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東漢大儒董仲舒的話。意思是說,做事情看重的是符合不符合道義,而不是看有沒有利益;看清楚了符合正道就應該去做,而不要計較結果。 朱子非常欣賞這句話,特地把它寫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指出這是“處事之要”,就是人做事的準則、要點。他說,我們做事,不是該怎么做就怎么做嗎?哪里先要苦心設計(安排)、編排拼湊(紐捏),還要搞點權術心眼(機械,即機心),才叫做事?何況我們都是普通老百姓,天下哪有那么多大事等著我們去做?我們做事的時候又哪里知道它的結果是什么呢?既然如此,我們卻平白無故地去畏頭畏尾、拈輕怕重,先就把事情弄壞了。 朱子說,我們做事要光明正大,光明正大的事就是符合道義的事,就應該去做,如果干什么事都是先考慮做了有沒有好處,那就會陷入功利主義的陷阱,結果反而一事無成。他認為,事情的“義”和“道”比結果重要,“利”和“功”是做正確之事自然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