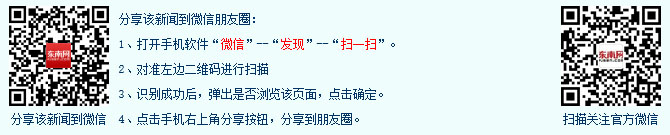|
文明是人類社會物質與文化的結晶,也體現物質與文化的氣象。理學家傳播文化、傳播理學,最終的目的是實現社會大同。雖然這個大同社會只是儒家、理學家的美好愿景,但千百年來,成為國人孜孜追求的理想目標。 物、理、心是宋代理學家研究最多的哲學概念。物是萬物(包括事物),理有萬理,但物和物之理都客觀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物和物之理向何處變化、發展卻操之于心。這個心是物和物之理的中心樞紐。如何運用這個心,儒家提出了一個重要方法——喜怒哀樂氣象為如何。朱熹說:“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中庸章句》)萬事萬物達到中和的狀態,天地各得其位,井然有序,萬物生生不息,這就是自然與人類文明的美好狀態。 理學家“遵德性而道問學”,無論是內求于心還是外求于理,都是為了中和。不同的社會制度的價值觀有所不同,但都有一個亙古不易的普遍法則,懲惡揚善、明辨是非、匡正去邪是古今共由之理,更簡潔的是一個善字。善,屬于儒家心性觀的范疇,在諸論中居首要地位,也是是非、正邪的一個重要砝碼,它包容廣大,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義利觀都在其中,并且操之在我。我之心即宇宙之心、天地之心,有此心物與物之理才能向上向善。 宇宙之心、天地之心,與生俱來,不能與物和物之理齊觀。上古時代,物匱民貧,卻有心性之養。三代(夏、商、周)鼎盛之時,心性覆載天地之間,“以遂其性”。(《宋史》卷四二七“道學一”)可見,心性具有天然的本質,有此心性才有“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的文明狀態。 心性之法不會自然流布于物和物之理,需要人的匠心獨運。朱熹說:“土地本生物養人。”(《孟子集注》)這是天地之性,但是順物之性而養,還是爾虞我詐而養頗有心法。朱熹說:“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論語集注》)“道不難知”“隨處發見”(《孟子集注》),人之性需“見于動作威儀之間”(同上)才能落到實處。儒家教人的心法是獨善其身,以己之善及人之善、及天下之善。朱熹在解釋孟子說的“善士”時說:“言己之善蓋于一鄉,然后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于一國、天下皆善。”(同上)這是理學家的高明所在。 文化的目的在于敦化風俗,獎掖先進。楊時、游酢不遠千里“程門立雪”,為的是“庶彰文明之化”;羅從彥“鬻田裹糧走洛”,為的是“天下有風俗”;李侗“崇正教”,為的是“善民俗”(明?費宏《新建李延平先生祠記》)、“鳳凰千仞耀文明”。(明?方岳《延平書院》) 大千世界繁復紛擾,唯有發明本心、細觀萬物、明察物理,方能繪出萬物華彩。上下五千年中華民族的文明史證明,最好的名片是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