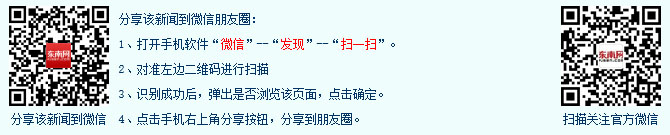|
詩曰: 勝日尋芳泗水濱, 無邊光景一時新。 等閑識得東風面, 萬紫千紅總是春。 換言之:美好的日子里尋春泗水河邊, 無限的風光景物一時都換上了新顏。 很容易就認清了東風真實面貌, 因為百花萬紫千紅都是春天的景致。
《春日》是首風景詩。王相注釋《千家詩》時認為它是踏青之作,描寫了春和景明的生動氣象。作者構思宏大、邏輯縝密、語言清麗。首句點明時間、地點、目的。“尋芳”二字表明了主題,也交代了下面三句都是其結果。詩人“尋”到了什么呢?天上人間,煥然一新,這是第二句。第三句轉為議論,說明“尋”的目的是“識”。最后一句則是對“尋”和“識”作了總結性的描繪:“萬紫千紅”既是春天的美景,又是讓人們認識東風的原因所在。“萬紫千紅”對應“無邊光景”,既把“尋”落到了實處,又自成對偶。讀之,頓覺春天轟轟烈烈,來了。 朱子寫下《春日》這首詩,也寫下了在古詩中吟誦春天的地位。人們例舉此類題材詩歌,《春日》是繞不開的話題。名家寫春,大都從具體事物著筆,或柳、或綠、或水、或花、或鳥、或人。美的感覺只是“草色遙看近卻無”。而朱子卻著眼于宏大,對春作全景式的描述。無邊光景,萬事萬物,生生不息,歡天喜地。《春日》感染了從牙牙學語的兒童到社會各界人物。習近平總書記訪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演講時就引用了“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的詩句。 《春日》實際上是哲理詩。“泗水”乃孔子傳道講學之地。朱子并未去過,當時也無法前往。“靖康之亂”后,南宋與金國以淮河為界,隔江而峙。孔子弦歌講誦的圣所早已腥膻一片。朱子“尋芳”尋的是孔孟圣人之道。這個學說廣大精微,奧妙無窮,“萬紫千紅”,引人入勝,一旦把握圣學底蘊,則心曠神怡。黃坤先生則從另一個角度解釋,“在這首詩中,晦翁(朱子)諭人,仁是性之本,仁的外觀就是生意,所以萬物的生意最可觀,觸處皆有生意,正如萬紫千紅,觸處皆春。”朱杰人教授說,黃坤先生的讀后感,“確實是啟蒙發覆之論”。有人稱孔子學說,仁學占了一半;孟子學說,大半是仁學。朱子專門撰寫了《仁說》。朱子論“仁”歸納而言就是兩句話:“仁”是心之德,愛之理;仁是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是儒家前賢所說,而“人物以天地生物之心為心”則是朱子的發展。他還舉例說明,“謂如一樹,春榮夏敷,至秋乃實,至冬乃成。方其自小而大,各有生意。到冬時,疑若樹無生意矣,不知卻自收斂在下。每實各具生理,更見生生不窮之意。”朱子眼中的春日是儒家生意盎然的世界。
理學家大都能詩,不過佳作不多。北宋大理學家程顥的“云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之《春日偶成》,已屬上乘之作,但與朱子的《春日》相比,高下立見。理學家們寫的哲理詩,其傳統可溯到魏晉時代的五言詩,評論家認為“淡乎寡味”。宋代以議論入詩蔚然成風,大都“硬語盤空,生拗峭奇”,說理有余,詩味不足,就像“有韻的哲學講義”,最為典型的“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言性”寫心,反對言情,成為“語錄詩”。因其字康節,人們譏諷他的詩為“邵康節體”。同為理學大家的朱子,一掃此詩風,開創哲理詩的新局。他以鮮明的形象寓理,在一個個生動的具象中,從容隱喻說理,讓山水與哲理聯姻。正如后人所評價那樣,有“理趣”而無“理障”。對“邵康節體”十分反感的錢鐘書說,“假如一位道學家的詩集里,肯容些許‘閑言語’,他就算道學家中間的大詩人。例如朱子。”《春日》沒有半句議論影子,卻又句句講“理”。寓“理”于生動形象的比喻之中,就是議論的第三句,也把“東風”擬人化了,全詩生動有趣。 《春日》還是“為己”之詩,反映了朱子成長的故事。朱子不是天生的儒學大家。劉述生教授說,“朱子的思想規模宏大,發展的過程屢經曲折。”朱子這首詩可以說是其思想認識第一次飛躍的代表作。朱子自幼所受的是“儒家式”的教育,“每天讀大學中庸之書,用力致知誠意之地”,但“某舊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其文并不排斥佛老。朱子曾言,“生君子少喜學,物外高人往還。”父親所托的五夫“三先生”,按全祖望所說,“三家學說略同,然似皆雜于禪”。據說朱子參加科舉考試,行李中帶了禪師《大慧宗杲語錄》,而殿試之時,竟然用禪家語錄應試文。同時其參空絲毫不下于禪學。夜宿武夷宮,隨口吟出“閑來生道心,妄譴慕真境。稽首仰高靈,塵緣誓當屏。”任職同安主簿后,仕途上的一切并未引起朱子興趣,還是儒釋道同修。他把官廓中一座軒閣修繕后題為“高士軒”,向往超然塵世之外的生活,后來結集的《牧齋凈稼》中禪道氛圍甚濃,直至遇到一位儒學大家后,朱子的思想和心理才發生了重大轉變。 正像李侗拜羅從彥為師時一樣,朱子問道延平先生也是24歲。李先生與朱子父親乃同執,共師羅從彥。朱子少小就已見過,且心生仰慕。從24歲這次相見開始,朱子與李侗有了十多年交往,經歷了有所懷疑、正式拜師、共同切磋、教學相長的過程。陳來教授考證兩人交往情況歸納成三個方面。“第一,癸酉朱子見李侗時,受到李侗的批評,但當時朱子卻懷疑李侗不懂禪學,心疑而不服……第二,朱子雖心疑李說,但還是聽從了李的勸告,專心讀圣賢之書,他對禪學當時的態度是‘權倚閣起’,‘且背一壁放’……第三,經過在同安的一段時間反復思考,認識到禪學之非與儒學之正。”錢穆先生認為李侗對朱子所教有“三大綱”:“一曰須于日用人生之融合。一曰須看古圣經義。又一曰理一分殊,所難不在理一處,乃在分殊處。”李侗給朱子最大的影響是,讓他看清了儒學佛道根本的區別,堅定了自己追求儒家圣人之道的立場,壯士斷腕般徹底地“盡棄異學”。從而在儒學的道路上“勇猛精進”。 朱子與李侗的交往有幾個方面值得說明:朱子出入釋老并沒有放棄儒學之根本。我和陳來教授談及“逃禪返儒”的表述時,他就不以為然。朱子留心禪學,問及道家是有原因的:一是他當時廣泛的求知欲;二是耳濡目染先賢的作為,認為釋老與儒家學相合,也是“為己之學”,似可作為追求儒家圣賢之道的門戶或者入道之助。不過,正因為有了朱子出入釋老的經歷,所以知己知彼,批判起儒釋學說最為有力。錢穆先生說,“朱子識禪甚深,故其辟禪,亦能中要害。”宋時佛道盛行,不少理學家漫淫其中不能自拔,“故諸子辟禪,其實乃所以矯理之流弊。”在這方面,朱子倒是不遺余力,功不可沒。還要說明的是,朱子尊崇李侗卻未盲從。李侗思想源流可追及羅從彥、楊時和大程子程顥。他們注重直覺主義的內在體驗,形成以靜為宗的學派,追求“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的氣象。朱子獨立思考,繼承李侗又發展了李侗的思想,沿著并不完全相同的路線,建立起獨特而龐大的理學大廈。劉述先教授這樣描述,“延平自有其一貫之理路,但朱子由禪道翻出來,歷經周折終于拋棄了以避世為高的思想,而體證到‘萬紫千紅總是春’的境界……朱子不甘于李侗之言,打破砂鍋問到底,這造成他業績之大處。但他卻發展出一特殊形態的思路。”當然,這是后話。
《春日》中表現出的朱子喜悅是巨大的,幾乎鋪天蓋地。與之前特別是同安任上的心情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在此之前,找不到孔孟圣學的入門要領,泛濫釋老,馳心空妙之域,常常有高揖辭世之嘆,心情悲苦,以至把仕宦感同“形役”,像“坐牢”一般。他問學李侗前后的兩首詩,最能表達朱子心情的變化:拜見李侗前的《月夜抒懷》,結尾為“抗志絕塵氛,何不棲空山。”以皓月當空、秋床獨眠、金桂飄香,高梧滴露,天風散發等意象,襯托高人逸士孤芳自賞與悲涼落寞的情懷。而在與李侗交往后的《教思堂作示諸同志》結尾中寫道,“塵累日以銷,何必棲空山”。詩中將儒家圣賢作為吟誦對象,雖是秋風已起,但天高氣爽,清涼滿窗。喜觀士子來來往往,讀經論道,仰慕孔門圣賢顏淵,追求曾參“風乎舞雩”的氣象,所有的疲倦懊惱一掃而光,“鶯飛魚躍”“何必棲空山。”劉述先教授評點這兩首詩說,看出朱子的“態度轉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彎”。陳來教授則言,“不僅說明他已一意歸向儒學,也已充分說明他已覺得‘圣賢言語有味’,這邊味長”。歷史地看,朱子的喜悅不僅是他自己的,也是文化的,我們的。(張建光/文、吳心正等/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