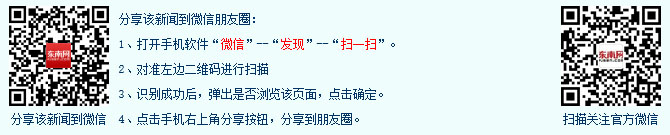|
說過年簡單也簡單,寫副對聯往大門兩邊一貼,放一串鞭炮,大門一關,一家人團團圓圓吃頓年夜飯,這年就算過了。說過年不簡單也不簡單,為了這餐豐盛的年夜飯,半個月前就開始忙乎了,房前屋后清潔衛生,買魚買肉做年糕年果,臨過年這天還得圍著灶臺轉一天。該上桌的大菜全搬上桌,吃不了飽個眼福,圖個熱鬧祥和氣氛。為了這個年,許多漂泊異鄉的游子,也得輾轉萬里,風塵仆仆趕回家。 小時候,我非常喜歡過年,因為過年媽媽會幫我買新衣服,讓我從頭到腳“舊貌換新顏”。口袋里有屬于我的壓歲錢,用這錢買燈籠、買彩炮,買自己想買的東西;過年我還可以享受到赦免權,如打破一塊碗,損壞一件東西,媽媽決不會罵我、打我,要在平時,犯這樣的錯誤,媽媽是絕不會輕饒我的。過年我還可以吃許多食品,如地瓜片、包米仔、凍米等,吃完了大大方方去鐵皮箱里取,用不著向媽媽“請示”,更不用背著媽媽去偷吃。過年,媽媽還教我許多吉利話,如吃年糕,要說“年年高升”,吃肉丸,要說“圓圓滿滿”,吃魚說“年年有余”,吃餃子說“招財進寶”,這些吉利話,讓過年增添了不少喜慶色彩。 幾十年過去了,我成了持家主事的大人,過年時的歡喜心漸漸淡了,一種怕過年的感覺襲上心頭,原因挺簡單,幾片工資養家糊口還要精打細算,年關一到,請貼一張接一張來,應付這禮尚往來的人情投資就夠我喘不過氣來。過年沒多有少總得備些年貨,為老少添幾件新衣,買些拜年禮品,一出手便是幾十上百,口袋一空,人的精神就振作不起來,但年難過年年過,你怕也罷,不怕也罷,年總是要過的。 現在的年,終究還是比過去的年好過了,也過得好了。且別的不說,過年時,放的那串鞭炮,炸得天響,響得排山倒海。看看人們過年時穿的、戴的,筆挺、油亮,個個帥氣精神。過完年,可以圍著電視機看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可以上街看放焰火,可以看露天的節目演出,還可以放心玩上幾天。大拜年、大串門、聊大天,我想,只有這樣的年景,才能過上這樣的年,這年是往后好年景的好起點,好兆頭。 上世紀七十年代,過年被涂上很濃的革命色彩。生產隊上山搞副業,忙到年底才下山,算工分搞分紅,多是利用晚上加班加點完成的,等到一百、二百元票子分紅到手,過年已迫在眉睫,匆忙間買點年貨,就算打發一年了。正月初一、初二拜拜年,串串門子,初三就得高扎褲管,清理豬圈牛欄,把糞肥挑去肥田。那時時興“農業學大寨”,出大力、流大汗、大干快上,連過年也沒有閑的時候,可日子過得還是緊巴巴的。不像現在,沒過元宵,田里是找不到村民影子的,盡管汗沒流得過去那么多,田里糧食長得不比過去少,年倒過得比過去豐盛,玩也比過去玩得開心。 過上第一個自在年,是1980年。那年,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自己責任田自己種,自家自留山自家管,沒有生產隊集體出工,集體收工的束縛,干起活來自由,掙的票子也多了,過年時,家里宰了一頭肥豬,粳米果也打了十幾石臼,直到來年的三、四月還沒吃完。記得那年吃年夜飯時,面對這樣的好年好景,父親觸景生情地給我講了一段故事:抗日戰爭勝利后的一年,國民黨反動派對蘇區實行“三光”政策,反動民團、大刀會時不時竄到老區基點村燒、殺、搶,搞得雞犬不寧。過年那天,細雨霏霏,父親正在村口水碓中舂米,朦朧中,看見水碓對面的山路上幾個穿蓑衣、藏短刀的陌生人,直朝水碓這邊鬼鬼祟祟地摸過來,父親意識到大事不妙,三步并作兩步從另一側小門溜出來,飛也似地往村里跑,一邊跑一邊喊“大刀會進村了!”村里人一聽,都顧不得收拾東西,一窩蜂地朝后山上逃。當父親跑到家時,家人正準備年夜飯,熱騰騰的菜在桌上冒著氣,無奈,全家人只好拋下這頓年夜飯,連一點值錢的東西都來不及帶走,就逃進大山。大年夜,本來高高興興的日子,全家人冒著雨,在一棵大樹下哆嗦地挨到天亮。正月初一下山回家一看,家中的牛被牽走了,豬被宰殺了,稍值錢的東西全被搶走了,年夜飯被大刀會的匪徒們吃得一精二光。父親說到這里,眼里閃著淚光。父親說,那年頭叫什么過年,叫遭災受罪,老百姓的日子就難過了。現在好了,過年總算像過年了。 這幾年我全家搬到城里過年,沒有像在鄉下時過年要先祭灶王爺,沒有點紅燭、插香火,日子照樣過得有滋有味。我相信:只要社會安定、國泰民安,往后的年景會更好,年年過年會更開心。(秋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