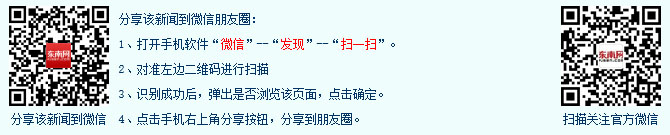|
農歷三月初三舊稱“上巳節”。古人在這天會臨水洗濯,消災祈福,祓除不祥,稱之為修禊。后來,這種祭祀活動逐漸演進為春日曲水流觴、飲酒賦詩的文人雅集。中國歷史上最知名的一次修禊活動,便是353年王羲之組織的蘭亭雅集。1913年3月,梁啟超在京城萬生園舉行的癸丑修禊雅集,表面上是對蘭亭雅集傳統的繼承,實則暗含著民國初年文化精英對傳統價值體系的重構訴求。在這場具有強烈象征意味的文化儀式中,福建籍士人群體以其獨特的文化姿態,勾勒出傳統文人在現代轉型期的精神圖譜。 當時參與萬生園修禊雅集的成員,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癸丑修禊集》卷首的照片統計有36人,另有饒孟任、陳懋鼎兩位參會但未合影。唱和諸公中,既有晚清遺老,亦有民國先進。其中福建文士9人,郭則沄等5位屬于當日參與者,且皆有分韻拈詩。侯官陳衍、嚴復和閩縣陳寶琛、林紓皆有受邀,只是因故未能參加當日雅集,但在雅集之后,陳衍、嚴復、陳寶琛均有補交追和題詠之作,陳衍另作《京師萬生園修禊詩序》,林紓則繪修禊圖記之。 這場雅集是梁啟超流亡返國后的首次重要文化活動,他自己也非常重視,畢竟“與蘭亭修禊之年同甲子,人生只能一遇耳”(《與嫻兒書》)。而在受邀名士之中,福建籍尤其是福州籍就占據五分之一強,這一方面說明梁啟超與閩籍名士交誼甚篤,另一方面更是說明即便遠在東南沿海的閩地,也成為當時文士精神和詩學思想的闡釋場域。 福建士人群體在此次雅集中的創作鮮明地體現出傳統文人的生存哲學,用陳衍在序文中的話,即兼具“經世之意”與“脫屣塵埃”之本心,“不以簪紱易其老莊山水之抱”。但在現實環境中,傳統文士很難在經邦濟世和吟詠山水間取得平衡,最終都會淪為“詩酒游娛是否有玩物喪志之嫌”的焦慮與掙扎。主辦者梁啟超在序文中極力抒發對于蘭亭雅集的欣羨之情,但同時又“徒顧影而悼嘆,寧假日以游娛”。可見,作為政治家的社會責任讓梁啟超在游玩唱酬中時刻保持著自省和警惕。 這種焦慮感在參會的福建名士詩作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陳懋鼎認為像王羲之、梁啟超這樣積極入世、才能卓越之文士,即便曲水流觴、詩酒唱酬,亦“非溺莊老風,乃悅山水妙”,因為“貴生將樂群,志遠惟靜照。祓禊特強名,由來釣非釣”,試圖借用詩酒風流之中寄托經世致用的弦外之音來消解其間的二元對立。而作為帝師的陳寶琛自然更是能在玄言清談的文學場合中發現深遠的政治抱負,“右軍故是溫謝流,臨河奄有嵇阮旨”,將王羲之視為與桓溫、謝安等匹敵的政治家。即便如此,陳衍的序文仍高度肯定延續蘭亭禊集之風的必要性:“以風雅道喪之日,猶復得此,可不謂盛歟?” 身處千年大變局中的雅集參與者大多兼具傳統士大夫與新式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如林志鈞作為北洋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長卻沉醉于碑帖臨摹,這種身份撕裂暴露了轉型期文人的精神困境。不過,傳統文人“經世之意”與“脫屣塵埃”兼具的生存哲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身為朝官而逃避世務的矛盾。而他們在詩會雅集中的文學實踐,既是對于傳統文化的承繼以及舊秩序的緬懷,同時也是在新語境下重構文化話語權的嘗試。 梁啟超雖然是近代維新派的代表人物,但是他非常注重傳統詩學,民國后與陳衍、林志鈞等閩籍文士過從甚密。1895年甲午戰敗,陳衍、林紓等在京城支持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公車上書;1898年康、梁等人發動戊戌變法運動,陳衍亦上書進言表示支持;民國初年,梁氏主編的《庸言》雜志連載陳衍的《石遺室詩話》,為后者宣傳同光體的詩學思想提供平臺。可以說,1913年上巳節的這次修禊活動,特別是八閩士人的高密度聚集,折射出晚清以來福建文化圈的特殊影響力,尤其是閩派同光體的詩學思想,通過這次雅集得到再次確認。 參與癸丑禊集的閩籍士人中,陳衍與陳寶琛是被學界公認的閩派同光體領袖,前者提出了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的“三元說”詩論,為同光體奠定理論基礎;陳寶琛則以“清蒼幽峭”的詩風為同光體的創作實踐樹立典范。圍繞在這兩位同光體領袖的身邊,還有一批或有親緣關系或有學緣師承的文士。郭則沄的父親郭曾炘與陳衍、陳寶琛關系密切;陳懋鼎是陳寶琛的親侄子;林志鈞早年詩學謝章鋌,后與陳衍、陳寶琛等同光體閩派詩人往來密切;林紓與嚴復雖不以詩名著稱,但同光體詩人的文化立場,與這兩位介紹西學最用力的翻譯大家頗為接近。學界普遍認為林、嚴詩風受到同光體的影響,可稱為宋詩派的外圍成員。由此可見,這種親緣、學緣交織在一起的地方網絡構建起嚴密的詩歌譜系。他們在癸丑雅集上的詩歌唱酬亦可視為對閩派同光體詩學主張的集體展演。 這場被歷史塵埃遮蔽的文人雅集,實為觀察近代中國知識精英精神轉型的重要切片。福建士人群體的文化選擇,既非簡單的復古守舊,亦非被動的時代棄兒,而是在文化斷裂處尋求接續的創造性努力。他們的徘徊與堅守,最終匯入了現代中國文化重構的復雜光譜之中。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