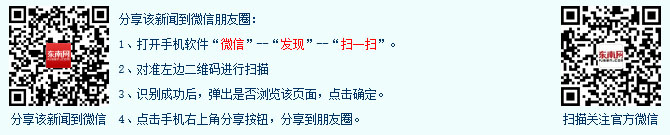對(duì)我來說,武夷山始終是個(gè)遙遠(yuǎn)的向往…… 平生走了很多城市,很多片山山水水,面對(duì)中國地圖,福建竟是我從未踏足的兩個(gè)省份之一,再有就是臺(tái)灣了。 我的工作地點(diǎn)在東北沈陽,福建的武夷山對(duì)我便是山遠(yuǎn)水遠(yuǎn)了,一直在等待一個(gè)機(jī)會(huì)去做武夷之行,尤其迷上茶道之后,便愈加向往那片山水。 我算不得茶道玩家,也并不癡狂于某一類茶,既非龍井控,亦非普洱迷,我喜歡一切好茶帶給我的不同的味覺體驗(yàn),一如去各處看不同的風(fēng)景,綠茶的風(fēng)輕云淡,紅茶的晚霞絢爛,巖茶的悠久厚重……特別是巖茶,我覺得一定要有了沉甸甸的人生經(jīng)歷后,才喝得懂它,那濃濃的火焙氣息傳遞出枯藤、老樹、昏鴉般的意境,通過味蕾,觸碰到了心靈深處,與心底那份滄桑融為一體。 今夏應(yīng)駐滬某部政委張德崇之邀,他便是武夷山人,經(jīng)不住他把家鄉(xiāng)描繪得仙境般誘惑,我們幾位女作家一同踏上武夷之旅,雖然高鐵把千山萬水從車窗外飛快地掠過,數(shù)千里路程濃縮在了8小時(shí)之內(nèi),但在我心中,卻有種走行了生生世世的感覺,一步一步接近那個(gè)深藏已久的向往。 在位于武夷巖茶產(chǎn)區(qū)的“父親母親的茶園”,天空時(shí)不時(shí)地下幾場(chǎng)熱雨,身旁清澗的山溪汩汩流淌,濃濃的負(fù)氧離子味道充溢在空氣中,侵襲進(jìn)你全身的每一個(gè)細(xì)胞,讓你的心像葉片一樣如醉如癡地伸展著……在這個(gè)茶園,傾聽干練灑脫的市茶葉局女局長鄧崇慧介紹武夷巖茶的歷史及如今的種植狀況,武夷巖茶的精耕細(xì)作注定了它的小眾化,高端化,武夷山市政府及武夷種茶人執(zhí)守著一種嚴(yán)謹(jǐn)而科學(xué)的態(tài)度,決不為追求產(chǎn)量而擴(kuò)大種植面積,在核心產(chǎn)區(qū),茶山頂端是從未開發(fā)的野生林地,中間地帶混種著果樹,坡下則生長著大片灌木林,用他們的話就是“頭戴帽,腰綁帶,腳穿靴”,正是這種近乎“半野生”的生態(tài)種植方法,造就了武夷茶那巖骨花香的獨(dú)特韻味。 茶園主人陳春龍帶領(lǐng)我們觀看了巖茶的制作流程,一泡茶經(jīng)過二十多道工序,經(jīng)由二百多個(gè)工人數(shù)月的勞作才能誕生,采青、萎凋、做青、揉捻、烘焙、揀剔……你會(huì)覺得,就在這一雙雙手的捻動(dòng)間,在那隆重的炭熏火焙時(shí)刻,一張張嫩綠的葉片被揉進(jìn)了故事,揉進(jìn)武夷的歷史和傳說。其實(shí),一部武夷茶史就是武夷人的歷史,一輩輩武夷人艱辛的生存與繁衍,絕望和希望,都深藏在卷曲的油黑色茶葉里。 在故鄉(xiāng)沈陽的茶城,我認(rèn)識(shí)很多經(jīng)銷茶葉的茶商,陳春龍是我認(rèn)識(shí)的第一位種茶做茶的人,這位80后小伙子不同于那些精明的茶商,他對(duì)茶樹有種深入骨髓的虔誠和敬畏。第二天,因?yàn)榕R時(shí)有事,他不能陪我們?nèi)ゾ皡^(qū)觀看那幾棵高懸?guī)r崖上的大紅袍母樹,當(dāng)年,進(jìn)京趕考的書生暈倒在巖崖下,被僧人救進(jìn)旁邊的寺院,住持用巖崖上茶樹葉片制成的茶葉煮水喂給書生,次日居然病氣全消,輕松踏上行程,又在科考中一舉奪魁,獲皇帝御賜大紅袍,回故里任職,途中特意來到寺院拜謝恩僧,又跪拜茶樹,將身上的大紅袍披于茶樹,由此成就神茶“大紅袍”的傳世之名。 20世紀(jì)70年代,農(nóng)科所的專家成功地將大紅袍母樹進(jìn)行無性繁殖,今天,遍及武夷山產(chǎn)區(qū)的大紅袍均為母樹的克隆體,幾棵母樹已經(jīng)被保護(hù)起來,成為只供游人仰視的風(fēng)景了。那日,我們?cè)诰皡^(qū)游歷了大半天,著實(shí)有些累了,一想還要搭乘景區(qū)的車去看大紅袍母樹,望到大群排隊(duì)候車的游人,便興致全無,干脆不看了,回賓館。晚飯時(shí),陳春龍得知我們沒看母樹,第二天一早就開車來接我們,他說你們一定要看母樹,不看母樹不算到武夷。 下了車,還要頂著烈日在峽谷里行走很長一段路,終于走到了巖崖下,仰望母樹,它們生長在巖壁上,不高大也不粗壯,矮小普通的樣子,實(shí)在是貌不驚人,但它們至少在那里站立了360年,這是生命奇跡,也是生命圖騰。陳春龍熱情地招呼我們一個(gè)一個(gè)過去與母樹合影。做為茶園老板,整個(gè)春夏他都在接待四方來客,陪著每一位客人去看看母樹,那么,他也就反反復(fù)復(fù)地走在這條的長路上……我想,對(duì)于他來說,每一次母樹之行,都是一次虔誠的拜謁,都是一次朝圣,那是他心中的神樹。一個(gè)內(nèi)心有敬畏的種茶做茶人是讓人尊重的,你不由得信任他和他的茶。 帶著幾款武夷山的茶葉回到東北,卻一直沒有開封,收拾房子搬家,所有的茶器早在一年前就打好了包,與幾十只書箱疊放一起,竟然忘記裝在哪幾只箱子里。沒有好茶器,我就執(zhí)拗地不動(dòng)這些茶葉,好茶器之于茶,是一份禮遇,是飲茶人的一種人生態(tài)度,即便在家獨(dú)飲,也要講究儀式感。那天,運(yùn)了十來個(gè)箱包到新家,拆箱時(shí)竟露出久違了的茶器,特別是看到那只臺(tái)灣匠人手制的老巖泥茶壺,不由得驚喜萬分,壺是嶄新的,購買多年,卻從未使用,一把完美展現(xiàn)工匠精神和獨(dú)特個(gè)性的壺,也是有故事的,如果沒給它尋到一款氣質(zhì)相配的茶,隨便用普通茶來打發(fā),便是毀了它的聲名。老巖泥的渾厚悠久韻味,特別是它通身滯留著成器時(shí)的柴燒氣息,我一下子就想起“父親母親的茶園”,想起那間繚繞著炭火的木質(zhì)烘焙室,想起武夷巖茶那千揉萬捻的身世。 燒水開壺,凈手焚香,我拿出一泡武夷肉桂,投茶,熱水沖淋,茶氣激揚(yáng)的瞬間……狀元抖開了大紅袍,披掛給茶樹……我突然悟到武夷巖茶被歷代茶人推崇的魅力之所在,那便是蘊(yùn)藏在巖骨花香中的絕望和希望的故事,隨著每一次儀式般的泡茶、品茶時(shí)刻,亦融入每一位茶人對(duì)生命至純至真的感動(dò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