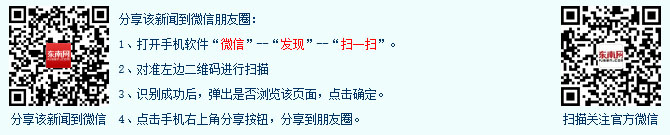“闕里諸孫圣代英,作官去拜四先生”(《翠屏集》卷二《送孔伯遜延平錄事》),這是元代福建古田理學家張以寧的詩。孔子的后裔孔伯遜到延平路(今福建南平)做官,張以寧寫了這首詩為他踐行。意思是說,孔子后輩子孫中,英才輩出,孔伯遜作為其中的一員,有幸成為“四先生”故里的父母官。張以寧希望,孔氏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去當地的先賢祠參拜這四位先生。“四先生”是誰?為何參拜他們,成了當地父母官的首要之務?
四先生即理學史上著名的“延平四賢”——楊時(1054—1135年)、羅從彥(1072-1135年)、李侗(1093一1163)和朱熹(1130—1200)。由于楊、羅、李三位都是南劍州(元代稱延平路、明代為延平府)人。其中,楊時是將樂縣人, 羅從彥是沙縣人,李侗是劍浦縣(今延平區)人,故又被稱為“南劍三先生”;而朱熹,祖籍雖為徽州婺源,出生地卻是南劍州的尤溪縣,故與延平也有密切的關系。在學術傳承上,四先生是一脈相承的師生關系。“南劍三先生”先后致力于二程洛學的闡發和傳播,為其后繼者朱熹開創“閩學”,集理學思想之大成,奠定了基礎,架設了由洛(二程洛學)至閩(朱熹閩學)的橋梁。
從大的方面來說,中華傳統儒學經歷了孔孟原始儒學,和兩宋程朱新儒學(理學)兩個大的發展階段。春秋末年,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奠定了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理論基石,既是中華傳統文化發展的主流,也是朱子理學的源頭。故當代著名思想史專家蔡尚思先生(1905—2008)有詩說:“東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國古文化,泰山與武夷。”泰山和武夷山,因為孔子和朱子,分別成為代表中國傳統文化高峰的兩座歷史文化名山;名人名山,相互輝映,孔子和朱子,則分別成為遠古和近古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個標志性的人物。
孔子所創立的原始儒學延至宋代,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產生了理學,又稱新儒學。所謂“新”,是指在理論形態上與傳統儒學相比,有其重要的創新之處。以朱子理學為代表的新儒學,是在孔孟原始儒學為主體的基礎上,吸收了佛教、道教,和歷代眾多思想家尤其是同時代的思想家的某些思想資料而發展起來的。
北宋是理學形成和初步發展的階段。理學先驅“宋初三先生”孫復、石介、胡瑗,奠基者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除周敦頤是江西人外,其余都是北方人。當時,福建雖有“海濱四先生”陳襄、陳烈、周希孟、鄭穆等倡道閩中,但從全國來看,影響有限。在理論水平和所影響的范圍來說,北宋時期的閩中儒學,遠遠落后于北方。到了北宋后期,全國各地的一些有志之士,紛紛到河南洛陽的程顥、程頤門下求學,其中雖然以中原和北方人士居多,但理論水平最高,且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方的兩位儒者,即福建延平將樂的楊時,和建州建陽的游酢(1053-1123)。
熙寧五年(1072),年方二十的游酢以鄉薦赴京應試,巧遇河南洛陽的程顥(1032—1185,字伯淳,號明道)。程顥對其資質大加贊賞,認為“其資可以進道”。游酢從此成為程門入室弟子。元豐四年(1081),游酢又與楊時拜程顥為師。兩人學成南歸之日,師生依依惜別,程顥目送他們遠去,滿懷期待地說:“吾道南矣!”意思是說,有了游、楊二君,我的道(理學思想)就可以傳到南方去了。武夷山一帶后來被譽為“道南理窟”,其淵源應追溯到游酢、楊時二人載道南歸,興學育人,促使理學思想在南方各省傳播,中國文化的重心逐漸由北向南轉移。元祐八年(1093),程顥已逝世八年,為了進一步鉆研理學思想,游酢又與楊時同赴洛陽從學于程頤(1033—1107,字正叔,號伊川)。游、楊二人于這年冬天冒著大雪來到程家,適逢程頤閉目瞑坐,他倆不忍驚動先生,恭敬地侍立一旁靜候,程頤發覺之時,門外已雪深一尺。從“吾道南矣”到“程門立雪”,代表了理學重心和中國文化教育的重心都將從北向南轉移的一種趨勢和歷史必然。
在中國文化史上,道教產生于本土,佛教則約在西漢末傳入中國,由于歷代統治者的大力提倡,極其盛行,對我國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道教在與佛教的論爭中也增強了它的思辨能力和理論水平,成為強大的中華本土宗教派別。儒、佛、道由之前的三家鼎立之勢轉為佛、道占據上風,一旦佛、道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使傳統的“以儒立國”變為“以宗教立國”,中國就有成為宗教國家的危險。為挽救江河日下的儒學的學術和政治地位,唐代韓愈、李翱等興起了儒學復興運動,提出恢復秦漢以來中斷了的儒學道統,以對抗佛、老之道。韓愈以孔孟道統的繼承者自居,激烈排佛,但他對傳統儒學繼承有余而創新不足,在理論水平和思辨能力上難以與講心性、重修持,極具思辨色彩的佛學抗爭,只能向高層提出建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韓愈《原道》,《唐文粹》卷四十三),即逼僧人還俗、焚毀佛書、把僧人趕出寺廟這種強權而低能的行政手段。
從治政者的角度來說,產生于北宋時期的理學思潮,在其發展的初期,雖對社會思想界有重要影響,但并未受到當時最高統治集團的特別重視。在崇儒的同時,北宋王朝也尊崇佛教和道教,且提倡三教合流,這就促成了佛、道二教的泛濫。下延至南宋時期,佛教更是成功地滲透到了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代表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儒家思想,面臨著更加嚴峻的挑戰。北宋后期,民族矛盾極為激烈,隨著北方大片國土被金人所占,北宋滅亡,復興和發展儒學的任務,被尖銳的民族矛盾所遮蔽,最終并未由周、張、二程等完成。
“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歷史的重任落在了朱熹的肩上!
張載(1020—1078)所提出的“為往圣繼絕學”的崇高理想,最終雖未由周、張、二程等人實現,但周敦頤(1017—1073)創立的“濂學”,二程創立的“洛學”,張載創立的“關學”,卻奠定了理學(新儒學)的理論基礎,也為南宋朱子創立“閩學”提供了豐厚而堅實的思想理論資源。由此可知,從濂、洛、關之學到朱熹的“閩學”,其發展與傳承源流,有一個從“北”到“南”的轉移過程。從時代來說,表現為從“北宋”到“南宋”的延續;以空間而論,則是從“北方”中原向“南方”福建的轉移。以人物而言,周、張、二程之后,則有游、楊、羅、李等先賢的學術傳承,最終有朱熹的集大成。
為了從理論上全面回應講心性、重修持的佛學的挑戰,同時也為了彌補先儒多重視社會政治倫理,而比較忽視心性之學的不足,朱熹率領門下弟子,以福建為中心,以武夷山為大本營,以南方各地創建和修復的書院,如武夷精舍、考亭書院、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等為陣地,高揚理學的旗幟,全面開展了重新詮釋和再造儒學經典的運動,從而使儒學經典,從原始儒學重《五經》,演化為宋明理學重《四書》的轉變;同時,也是為了彌補各地書院的不足,他們創造性地將書院的“旗幟”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從而形成了與理論上“援佛入儒”、兼采佛老之精粹相適應的儒學傳播實踐,即將佛教的圣殿和講堂演變成為傳播儒學的杏壇。
在朱熹等人的倡導下,在理論形態上的“斥佛老,一天人”,與物質形態上的與佛教爭奪教學陣地相結合,就成了其后儒家學者的共同行動。這便是為什么在南宋的理學重心最終完全轉移至福建并得以確立的同時,書院文化教育的重心也隨之轉移到福建的重要原因。
朱熹的歷史貢獻,可以用“返本開新”四個字來加以概括。所謂“返本”,是指朱熹全面系統地對孔孟以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如中國傳統經學、心性哲學、倫理思想、政治文化等方面都作了一個全面的總結。所謂“開新”,是指朱子在繼承程顥、程頤開創的理學思想體系的基礎上,根據時代的要求和理論的發展,與同時代各個不同學派的思想家相互交流、相互論爭、相互促進,又汲取先秦儒學諸子百家和佛、道思想之長,加以綜合創新,集宋代理學之大成,在理學本體論、心性論、格物致知論、倫理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等各方面把宋代理學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哲學的內涵,為中國哲學的發展,作出了杰出的理論貢獻。
由于朱子理學在維護社會穩定,鞏固和加強封建君主集權制服務,維護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方面,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從而得到晚宋以后歷代統治者的特別青睞。
宋寧宗嘉定二年(1209年),朱熹逝世九年后,將朱熹學說誣為“偽學”,將朱熹學派誣為“逆黨”的“慶元黨禁”冤案開始逐漸平反。這年十二月賜朱熹謚曰“文”,稱朱文公。(《宋史?寧宗紀》)嘉定五年(1212年)十二月,朱子門人,時任國子司業的建陽人氏劉爚的請求得到恩準,詔諭朱熹的《四書集注》立于學宮,作為法定的教科書。(《宋史?劉爚傳》)宋理宗時期,朱子的學說進一步得到褒揚。寶慶三年(1227年)正月,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宋理宗稱贊朱熹的《四書集注》“發揮圣賢蘊奧,有補治道”。紹定三年(1230年)九月,改封為徽國公。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下詔從祀孔廟。朱熹取得與周、張、二程并列的五大道統圣人的地位。詔書稱:“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后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圣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渾)融,傳《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宋史?理宗紀》)同時,又御書朱熹《白鹿洞書院揭示》,頒布天下學宮。
由于統治者和朱子后學對朱子學的表彰和宣揚,朱熹歷史地位確立,朱子理學上升為封建社會后期的官方哲學和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官方治國的指導思想。對中國社會政治、文化、教育、民俗等諸多方面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對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建構,對民族傳統思維方式的完善也有潛移默化的作用。正是在這個層面上,我們說,不能將閩學——朱子學視為是一種地域性的學說,而僅從閩北文化、福建文化這一層面來認識,而應該從這是一種帶有普遍意義的,在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政治哲學這個角度來評價和認識。也正是在這個層面上,國學大師錢穆認為,“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兩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曠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堪與倫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