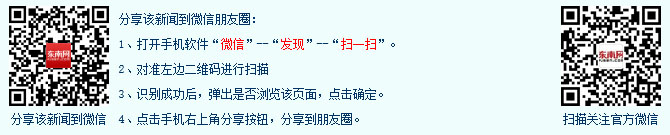|
2019年這個尋常夏季的下午,天游峰竹林里,微風黏著草木的清香,從驚人的青蔥翠綠中穿梭而來,讓我久浸濁世的塵心冒出一絲隱居在此的念想。而走近武夷精舍,看到四面絕壁的隱屏峰時,我的內心十分震撼和迷惑,朱熹為何選擇在峻嶺絕壁下修建書院呢?忽然,腦中跳出林則徐的名言“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嗯,偉人的想法總是驚人的一致! 穿過“武夷精舍”石牌坊往里走,眼前出現一座同期修建的仿古木構建筑。它是在武夷精舍遺址上重建的朱熹紀念館。難得的是,里面有一特殊展品是光緒年間的武夷精舍土墻,墻上保留原樣木窗。 游客們貼著玻璃墻認真地看著里面土墻,希翼著它能親口道出自己的悠久歷史,但一面土墻所包含的信息畢竟有限。我好奇地目測土墻的高度、厚度、材質,欲探知當年該書院建筑造價多少。誰建造的?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 欲知武夷精舍造價,先說它的第一個建造者朱熹。朱熹十九歲正月娶妻,四月金榜題名。人生三大喜,他同年占了兩樣,可謂青春得意,緊接著十二月在武夷山五夫里第一次收徒授課。二十四歲時,朱熹步入仕途,不依附權貴,清正有為。 宋淳熙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公元1183年),朱熹任浙東常平茶鹽使、浙東巡撫,不畏強權,六次彈劾貪官臺州知府唐仲友,因此得罪了王淮而被污蔑和排斥,不得不辭官歸故里武夷山。那時退職官員常主管觀事,以領取一半薪水。朱熹和陸游、辛棄疾是好友,都先后主管過武夷山沖祐觀。朱熹在主管沖祐觀時便親自籌劃營建武夷精舍。精舍內有仁智堂、隱求室、止宿寮、石門塢、觀善齋、寒棲館、晚對亭和鐵笛亭等建筑,成為武夷山享譽盛名的一大建筑,人稱“武夷之巨觀”。這也是他在國內創辦的多所書院中迄今為止最有影響力的一所。 武夷精舍建成后,朱熹寫信告知陸游。陸游寄來賀詩四首《寄題朱元晦武夷精舍》,其中一首是: 先生結屋綠巖邊,讀易懸知屢絕編。 不用采芝驚世俗,恐人謗道是神僊。 當時陸游因被趙汝愚彈劾而辭官賦閑在家已五年,得知武夷精舍建成,十分高興,卻寫這首詩戲虐調侃朱熹住在遠離塵世的地方,叫他不要去采靈芝嚇人,恐怕人家以為他神仙下凡。貌似是句玩笑話,其實弦外之音是贊美朱熹隱居做學問的行為,因為“絕編”的出處是韋編三絕,講的是孔子為讀《易》而多次翻斷了牛皮帶子的簡。后人就用“韋編三絕”即絕編、絕學來形容一個人讀書刻苦勤奮,也是博學的意思。 陸游在這首詩里用此典故還有另一層含義,朱熹在武夷山撰寫了一本巨著《四書章句集注》,算是隔代傳承孔子衣缽。陸游因此贊美朱熹的行為可謂是神仙,也是陸游所不能及的。當時朱熹也擔心陸游因支持韓侂胄抗金而關系太近會晚節不保。 慶元元年(1195年),宋寧宗即位后,趙汝愚推薦朱熹為宋寧宗侍講,卻因韓侂胄挑撥離間而罷免。朱熹在武夷精舍講學時,好友辛棄疾來拜訪他,稱贊他是:“山中有客帝王師”。正因為是帝王師,隨時一句話可動搖帝王的決定。韓侂胄為打擊政敵趙汝愚,獨攬執政大權,便指使同黨沈繼祖攻擊朱熹的道學是偽道學,致七十歲的朱熹含冤抱恨而終。 朱熹去世后,辛棄疾不顧身家性命安危,親自來武夷山吊祭,并撰祭文:“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陸游也不顧韓侂胄的警告,寫了一篇悲痛欲絕的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耄,神往形留。公歿不亡。尚其來饗。”陸游恨不得掏心掏肺地捐軀來換回朱熹的生命,說兩人因道路阻隔無法見面,但在陸游心中,朱熹是死而未亡。 今日我在武夷精舍牌坊下,回想陸游、辛棄疾為朱熹寫的祭文,內心異常悲痛沉重,也感佩于陸游、辛棄疾與朱熹之間惺惺相惜的深厚友情。尤其陸游和朱熹雖政見立場不同,卻也求同存異。這樣的友情是彌足珍貴,可遇而不可求。所幸,三位好友總算在文學史上殊途同歸,都成為千古流芳的文化名家。 當年在武夷精舍就學的許多學生都成為著名學者如蔡元定、劉爚、黃幹、詹體仁、李閎祖、葉味道等。南宋開禧年間,受到朱熹思想影響的多位理學家的理學著作在金國統治的汴京引起一流文人學者的重視,且與金源統治者尊崇、提倡儒家經典的思想基本一致,得到重視和傳播。寶慶三年(1227年),宋理宗下詔書,追贈朱熹為太師、信國公,提倡學習他的《四書集注》。此后,朱熹學說作為官方哲學,成為聲譽隆盛的顯學。 武夷精舍也得以擴建,改名為“紫陽書院”,由官府撥給公田以供養學者。元朝到清朝,武夷精舍經過多次修繕或重建。最后一次修建是光緒年間,鄉紳朱敬熙重修,立門匾“文公祠”。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解放軍192療養院進駐。文化大革命中,正堂被拆除建療養院會議禮堂。遺址僅存兩廡部分磚地與土墻。2003年,武夷山政府重建“武夷精舍”。 今天再對當年的武夷精舍建筑進行估價,便是無價。時隔八百年,“武夷之巨觀”雖建筑規模縮小了,依舊是武夷之巨觀。此“巨”非建筑之巨,乃思想、思想家、教育家之巨。朱熹作為宋明理學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不僅給予了中國思想界以極大的影響力,且是日本朱子學得以形成與發展的源頭活水。 時至今日,朱熹理學的精神內核依舊在爆發能量,影響之巨足以令人嘆為觀止。因此,武夷山成為理學名山,武夷精舍成為理學的圣地,但凡崇拜朱熹的人都會爭取一生至少來武夷精舍朝圣一次。其實這也不僅是對朱熹和理學的一種認可,也表達了對這位思想家、教育家、正直官員的一種崇敬之情。 因此,古往今來四方朝圣者絡繹不絕,武夷山的優美風景也因朱熹而名揚天下。但是,在思想家的光芒下,朱熹的教育家身份更應該被重視,尤其在21世紀的當下,有知識不等于有文化,如何保證優秀的文化學者和作家進入教育系統,應列入國家教育大計中。教育的作用也是武夷精舍之巨觀的另一層重要意義。 朱熹并非為教育而教育。他對教育的理解,在《四書集注》的序中寫得分明:“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宋代八歲入小學,比今天的六歲上小學要晚兩年,而且主要是教禮節。這一點,我深以為然,小學教育當如此更符合兒童天性又是基礎教育之重點。對于如何教學,朱熹又說:“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意思是要因材施教。 但朱熹不無遺憾地說:“周之衰,賢圣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周朝末年因教化不夠,百姓道德墮落。朱熹因此覺得當老師比當官更重要。作為帝王師,朱熹有許多精深思想希望為學生皇帝宋寧宗所接受。可惜,愚蠢的宋寧宗只喜歡聽甜言蜜語,而且如朱熹所言“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于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其實歷代不少學子都被教之死記硬背文句,即使上到大學也沒有形成個人思想。還有一些惑世誣民、假仁假義者學知識不是為了修身養性,而是為了知識改變命運即追名逐利。 宋寧宗不肯接受朱熹思想,除了自身能力平庸外,正是被很多沒有思想的俗儒包圍,才聽信了韓侂胄的污蔑而辭掉了帝王師朱熹。這就成為南宋悲劇后果之一。朱熹因此心痛不已,立志當一個教育家,挽救中國學子。從《四書集注》之序已足見朱熹思想之深刻。 中國歷史上儒釋道三教一直在打群架。朱熹把淵博的學識與卓越的哲學智慧巧妙地結合起來,是繼楊時、游酢之后,集兩程理學之大成者。理學促使儒釋道三教握手言和,打破了先秦諸子的思想禁區和漢唐以來的大一統桎梏,從南宋末年開始成為我國最有影響力的哲學系統。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元仁宗下圣旨以“四書”為國家考試的主課,以朱熹注解為官方解釋。從此,《四書章句集注》成為元朝至清朝欽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直至1905年廢科舉、興辦現代學校為止。 朱熹生前為了讓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被播種出去,不僅出去講學,還成為書院辦學的熱衷者。他為自己的學院訂立的校訓是“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他的理學思想順著書院文化的興盛,宛若長江黃河,縱橫流經祖國大江南北。 當我在武夷精舍周圍游覽時,情不自禁地感嘆自然造化之神奇。從天游峰往隱屏峰,一路奇石、溪流、松竹構成的天然幽雅讀書環境,是國內其它書院所不具備的。置身其中只想問道而忘肉味,難怪朱熹大師在此著述、講學。 但武夷山的第一所書院不是武夷精舍,而是建于北宋政和五年(1116年)的叔圭精舍。在我國,一個地方書院的數量多寡、規模大小及影響遠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個地方歷史文化地位的高低。由于武夷山是理學名山,書院文化氛圍濃厚,此后一批理學名家相繼在武夷山擇地筑室、讀書講學、繼志傳道,使得武夷山“書院文化”繁榮昌盛,曾有:屏山書院、興賢書院、崇賢書院、雙仁書院、寒巖書院、陽明書院·甘泉精舍、南山書堂、洪源書堂、幼溪草廬、留云書屋、胡文定祠、水云寮、仰高堂、九峰祠。 蔡尚思詩贊“中國古文化,泰山與武夷”。武夷書院栽培了大量學生,使武夷山在南宋時期成為祖國東南的一座文化名山,后人稱之為“閩邦鄒魯”、“道南理窟”。(孟豐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