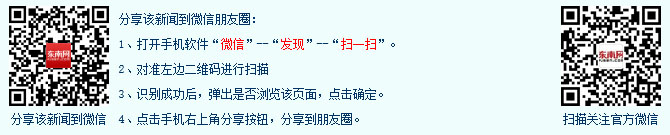|
說到武夷山,就不得不提九曲溪漂流。兩條竹筏綁在一起,由艄公撐著行于溪中,順?biāo)鞣较驈牡诰徘虻谝磺瑲v時(shí)兩個(gè)多小時(shí),行走十八道彎,一路下來看得多看得少,全在自己。 漂流碼頭設(shè)于九曲溪上游星村鎮(zhèn),碼頭三個(gè),相距不遠(yuǎn),可任意選擇,湊夠六人,即可登筏。與我們同行的,一對來自蒙古西旗的年輕人。另一對來自河南的老年人,女士腿腳似乎有些不便,拄著拐杖。我們六人搭配成老中青三代,有緣同筏漂流武夷山水。 看山水,古人說了三種境界,都在我們筏上。年輕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中年人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老年人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是不是這樣,我沒詢問那對年輕人和老年人。至于自己,我覺得既看到了山,也看到了水,它們真實(shí)地存在于自然,我真實(shí)地在它們里面。無非是人在山水間,或快或慢,起起伏伏,只可順流而下,不可逆流而上,滿眼風(fēng)景沒來得及細(xì)想,一路風(fēng)光就盡過了,像濃縮的一生。 艄公舉起撐桿,竹筏之舟輕松地漂進(jìn)了九曲溪,我們便如收攏了翅膀的蝴蝶,浮于碧水,不用飛翔勝似飛翔地飄向前方。此時(shí),閉上眼,仰躺在竹椅,深呼吸幾口,真甜,還有香味,這才睜開眼睛,去看這自然山水天賜美景。 艄公們賣力撐竹筏,保持平穩(wěn)。他們每個(gè)人練就了一副好口才,除了景點(diǎn)傳說介紹,還加入不少段子,讓觀光客笑聲不斷。比如把筆架峰形容成三個(gè)代表:電表、水表、煤氣表。把武夷山三十六峰、七十二洞、一百零八廟,在這些艄公們嘴里或詼諧、或幽默,在生動中又能體會他們的不易和辛勞。 坐在幾根竹竿上漂流,屁股需要專注,認(rèn)準(zhǔn)了坐下,不能亂換座次,否則容易落水濕身。坐在上面,思緒萬千,比如美景、美事,比如華茲華斯之類的詩人等等。華茲華斯的詩歌不是我喜歡的類型,但我向往華茲華斯熱愛山水、鐘愛自然的執(zhí)著和勇氣,雖然沒有能力效仿。據(jù)統(tǒng)計(jì),華茲華斯一生走了一百七十五至一百八十英里路程,每天在鄉(xiāng)間和湖區(qū)行走,很多鄉(xiāng)下人說他走路像只大谷盜蟲。那是一種斜著行走的昆蟲,類似螃蟹,或類似我坐的竹筏,斜行九曲溪之中。別扭的行走卻給詩人帶來靈感,成就了他關(guān)于大自然的詩作,如《致蝴蝶》《致布谷鳥》《致云雀》等等。城市的烏煙瘴氣、擁擠、貧窮和丑陋,讓華茲華斯抱怨,1789年夏天,詩人和他的妹妹再次來到威爾士的瓦伊河谷,親身體驗(yàn)了自然的力量,并在隨后的詩作中流露出來,伴隨了詩人的一生。今天,在武夷山九曲溪漂流,我會不會體驗(yàn)到神奇的自然之力呢? 行于溪上,坐看武夷山巒,大大小小從眼前飄過,飽覽美景之余,免不了生出恍惚感。這感覺來自周圍的巨大空間和一個(gè)人蜷縮竹椅中的反差,有帕斯卡爾《沉思錄》所說的“被無垠的空間吞噬”的驚恐。我在其中嗎?這問題有點(diǎn)蠢。可是,武夷山水如何知道我在其中呢?我來過,我們來過,但這些山山水水不曾記得,最終我們自己也會遺忘。古人們把他們表達(dá)來過這里的字刻在石頭上,刻得很深,躲開了歲月的消磨,留存至今,我們看到了他們,可他們看不見自己。忽然明白華茲華斯鼓勵我們走進(jìn)大自然,體驗(yàn)真情,滋潤魂靈的重要。大自然面前,人類其實(shí)很渺小。 一隊(duì)隊(duì)竹筏滿載一批批旅人,前來又遠(yuǎn)去,玉女峰在九曲溪某個(gè)彎道上,沉默地目視他們靠近又目送他們遠(yuǎn)離。或者,她什么都看見了,或者,她什么也沒看見。加在她身上的傳說,是個(gè)美麗動人的故事,隨風(fēng)飄散,流落民間,廣為傳播,只有她只字未提。 當(dāng)玉女峰、大王峰逐漸消失于視野,我再一次肯定所經(jīng)歷的山水,絕非人的創(chuàng)造。人類只能將其想象附著在它們身上,讓自身演繹悲歡離合。可是它們,那些巨石,并不為之動容。最終,物質(zhì)論者在無奈中,只能從編造的神話中持續(xù)物質(zhì)索取,而非精神奉獻(xiàn)。 我們常說人在畫中游,因?yàn)榭吹搅俗陨聿痪邆涞淖匀恢馈N覀冊诰徘F(xiàn)實(shí)主義的畫中漂流,體驗(yàn)到不同程度的快樂,并且沉浸在自身的快樂之中。如果我們看到的是一幅現(xiàn)實(shí)主義畫作,它源遠(yuǎn)流長的寫實(shí)是不是表達(dá)了一個(gè)真實(shí)存在的世界?這世界是永恒還是瞬間?我們留下了永恒,帶走了瞬間,還是帶走了永恒,留下了瞬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