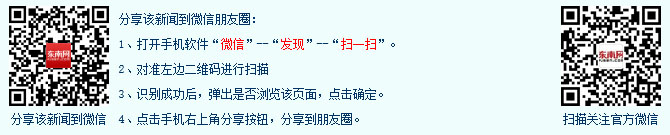|
張建光是我的老朋友,他長期在南平地區工作生活,他的文學創作刻上了鮮明的地域特色,尤其是朱子和朱子學,成了他文學創作的主體。但也恰恰是朱子和朱子的思想造就了一位以獨一無二的敘述方式、以詩一般的語言講述朱子、研究朱子的作家和學者。特立獨行,以這樣的文字寫朱子,建光大概是第一人。 三年多的疫情,他交出了一部力作:《朱子的詩和遠方》。這是一本研究朱子詩歌的學術著作。朱子是一位詩人,他最早被介紹給皇帝不是以思想家、哲學家的身份,而是以詩人的身份。可見,他的詩是很早就被人認可的。他的詩作有十卷之多,凡詩之體,如詞、賦、樂府、古體、近體無不涉及,儼然大家,不容小覷。但是,因為他的理學成就太高了,詩的光輝被掩蓋了。 讀了《朱子的詩和遠方》,我為之一振,一位當代的詩人關注了朱子的詩,并用他特有的敘述方式交出了他的研究成果。 我已經再次提及此書的“敘述方式”。什么是建光的敘述方式呢?這種敘述方式是:不用純理性的、純理論的、純學術話語的敘述,但又不失理性、不失理論、不失學術話語的敘事與論述。這應該是建光的創造,但這種創造是建立在深厚的文學修養和超強的語言能力與學術涵養之上的,一個純學者做不到這一點,一個純作家也不可能做到。 本書的開篇之作《遠游天下》恐怕是這一敘述方式的典型代表。 請看:“年方十九的朱熹手擎酒盅,緩緩來到大廳中央,面對眾多親朋好友,包括高堂老母和新婚的妻子宣布”他要遠游了。 請看:“聽吧,這是朱子遠游的心聲。像大鵬展翅,像駿馬奔騰,扶搖而上九萬里,視九州為咫尺。”“看吧,這是朱子遠游的雄姿。” 這是以詩解詩。 在分析此詩的藝術特點時,他說:“《遠游》一詩,直抒胸臆,情感激烈。這在朱子千余首詩中并不多見,與其一貫追求的‘蕭散沖淡’詩歌主張也不相符,因而《遠游》一詩在朱子詩詞中擁有獨特的意義。” 這是以理解詩。 “朱子引屈原為異代知己,自覺與他心靈相通。《遠游》是朱子最早的詩作之一,而他去世前三天,修改完《大學誠意章》后,又訂正《楚辭集注》。聯想起兩人共同的坎坷仕途和多舛命運,心中不免生出唏噓感嘆幾許!” 這是以史解詩。 下一篇《春日之喜》也有異曲同工之妙,他把一首《春日》詮釋得詩情畫意如在眼前,詮釋之詞也是詩了。 接著,他要講哲理詩了。 他說:“《春日》實際上是哲理詩。”“朱子眼中的春日是儒家生意盎然的世界。”“他以鮮明的形象寓理,在一個個生動的具象中,從容隱喻說理,讓山水與哲理聯姻,有理趣而無理障。”但是,又不僅止于詩,在這一篇中,他以《春日》為由,講到了朱子哲學思想的演變與發展,講到了朱子對李侗思想的繼承與發展。他說:“朱子獨立思考,繼承又發展了李侗的思想,沿著并不完全相同的路線,建立起獨特而龐大的理學大廈。”必須指出,講朱子的詩,恐怕離不開他的理學思想,但是如果把論詩寫成哲學講義,那就不是講詩而是上哲學課了。建光先生的過人之處在于他既懂詩又懂理學。他能把理學與朱子的詩有機地糅合在一起,借朱子的詩說理,又以理證詩,從而使理充滿了詩意,又使詩的內涵得到無限的伸張。這從《半畝方塘》《鵝湖詩會》(順便說一句,建光認為鵝湖之會是學術之會,也是一場詩之會。這是一個全新的視野,令人激起研究的沖動)《九曲棹歌》等篇章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如果有人要了解朱子理學卻怕理論的艱澀枯燥,《朱子的詩和遠方》可能是一本會令你饒有興趣的入門讀物。 建光先生研究朱子的詩,有一個“訣竅”:以朱子詩作的重要意象入手。他準確地抓住了春、雨、雪、云、梅、茶等意象捕捉到詩人心靈的脈動與興發、形象與意境,把讀者帶入到詩所要表達的情景與內涵之中。比如雨,他說:“朱子詩中多雨。捧起詩箋,心里頓生溫潤。細細檢點,以雨為題的詩竟有33首。”“朱子的雨詩,覆蓋了歲月季節,也摹寫了發生的全過程,更寄托了人生情感:春雨、冬雨;雨前、雨中、雨后;驟雨、小雨;雨打枝葉、雨入方塘;觀雨、對雨……”他還發現,朱子的雨詩,以三十歲為界形成兩種景象:前者多,后者少;前者幽,后者白。他還從朱子的雨詩中看到了以民為本和視民如傷的情懷。又比如雪,他發現“雪幾乎是他(朱子)詩歌中的第一意象,以此為題的詩近四十首。”他說:“雪在朱子的心目中純潔高尚,”“朱子把冰雪的高潔當作自己精神的圖騰,就像他在‘圣賢氣象’(筆者按,《近思錄》的一章)中所談到的‘光風霽月’、‘溫潤如玉’一樣。它是儒家思想的最好表征。”也許是因為建光本人就是詩人,對詩的理解比一般人深,所以他能找到一條最好的路徑和切入點。 對朱子詩作的認識與朱子詩歌創作理論的探討,主要集中在全書的第一章《詩人朱子》中。 開篇第一句話:朱子一生對詩“若即若離”,十分矛盾。 我理解,這句話是說,朱子一生離不開詩,但又對詩保有“戒心”。這是有史實依據的。朱子不讓自己的兒子寫詩。但是當他的長子(朱塾)不幸夭折,他在整理遺物時看到兒子的詩作,發現兒子的詩寫得非常好,他不禁長嘆后悔,不應該阻止朱塾寫詩。也許人們會不滿朱子的“專制”,但是如果你了解了朱子對學詩、寫詩的苦心以后,你的不滿也就釋然了。朱子構建新儒學,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不滿自孟子以后儒學陷入了章句、訓詁的教條,唐以后又陷入了詞章之學的窠臼。所謂“詞章之學”,就是專注于詩詞、文章,而丟棄了為學的根本--儒家的義理和為己之學。唐代以詩賦取士,宋代因襲之,更加重了這種學風的泛濫。學子們把畢生的精力花在如何寫詩作賦上,而不鉆研儒學的經典,是舍本而逐末。再則,詩到了唐以后格律化已經成熟,要寫出一篇合律的詩,不經過嚴格的訓練是根本做不到的。更重要的是,朱子認為,詩是一種特殊的文體,不是人人都能為之的,除了要有一定學問的鋪墊,還需要某種天賦。所以他不主張人人都去寫詩,與其花大量的時間去做寫詩的工夫,不如好好地去讀儒家經典,做正心誠意的功夫。當然,那些具有詩人天賦的人除外。所以,在他還沒有發現自己的兒子是詩才時,他勸兒子不要寫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但是,朱子自己卻離不開詩。建光兄說:“以‘矛盾’觀朱子,他幾乎把生命一分為二:一半予道,一半予詩。”這個結論有點夸張,但基本如實。 在開篇之章中,作者首先討論了朱子的“詩教”理論,進而論證了他的文道觀。他指出朱子主張文道合一,詩理和合是其理論核心,“不能離道言文,亦不能有文無道。他始終堅持文學形式和內容的統一。”這個結論是公允的。作者又認為,朱子“看重平淡詩風,厭惡浮薄華糜,纖巧柔弱之作。”這也是符合實際的。 建光兄在研究朱子的詩學理論與創作實踐時有一句話,我特別欣賞。他說:“所有朱子詩歌的矛盾問題,一進入朱子創作實踐便圓融解決。”我想,這樣的結論如果沒有對朱子詩論的通透把握,沒有浸潤于朱子的作品之中,是無論如何也講不出來的。如關于“方塘詩”的理解,如對于《九曲棹歌》的爭論,就是這樣在他的筆中迎刃而解的。 關于哲理詩,是朱子詩歌中的大宗,也是爭論分歧較大的問題。作者認為,朱子的哲理詩達到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取得這樣的成功得益于朱子始終堅持情感為詩生命的立場。這是一個很有見地的發現,它解決了關于哲理詩如何才能是詩而又具有哲理的理論問題。值得引起關注。 大約一年前,我有幸與建光兄在建陽面晤,頗有一點感慨。他拿出一本書稿,要我寫序。我不能推脫。在返滬的高鐵上讀了他的書稿,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更產生了想寫的沖動。我不敢說我一定能不負老朋友的重托,但,心悅誠服的盡力卻是一點不含糊的。于是有了以上的文字,權作序言。狗尾續貂,請建光和讀者諸君見諒了。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中國考亭書院山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