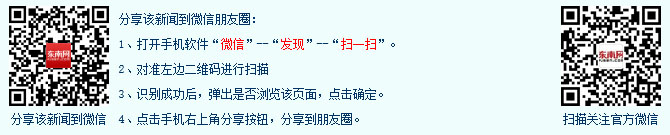|
徜徉九曲溪畔隱屏峰下,環(huán)顧新落成的“武夷精舍”,朱子難掩喜悅,一氣作“精舍雜詠十二首”。開篇曰: 琴書四十年,幾作山中客。一日茅棟成,居然我泉石。 “武夷精舍”在山中構(gòu)仁智堂,左建隱求齋,右搭止宿寮。另辟竹塢,累石為門,塢內(nèi)興觀善齋,門面筑寒棲館。山巔立晚對(duì)亭,臨溪站鐵笛亭,前山口拉起柴扉,掛上書院的匾額,至于飲茶的“茶灶”,就以溪中的一塊巨石充當(dāng),上無片瓦半木……簡陋如此卻稱“精舍”,原因在于朱子匠心獨(dú)運(yùn),除了帶領(lǐng)學(xué)子“勤工儉學(xué)”營建外,還有就是書院所處的位置和“精舍”的象征意義:武夷山水人文精華盡在九曲溪,九曲又以五曲為勝,書院便坐落于此;人住的地方是宿舍,靈魂所寓當(dāng)為“精舍”。 朱子吟武夷精舍的詩得到熱烈的反應(yīng)。董天工在《武夷山志》列舉了52位“和”詩。其中不乏大家,如陸游、袁樞、楊榮、陸廷燦、薩天錫等。詩歌也給朱子帶來了麻煩,政敵們抓住“居然我泉石”之句,攻擊他有獨(dú)占武夷山之意。朱子“昨關(guān)目思量,許多紛紛,都以《十二詠》首篇中-‘我’字生出。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斫不倒,觸處作災(zāi)怪也!”他后悔遣詞造句的隨意,卻不悔不改興辦書院的初衷。 朱子擁有濃郁的書院情結(jié)。與他有關(guān)的書院有67所,成千上萬學(xué)生為他親炙,陳榮捷教授考證的正式注冊(cè)有名有姓的就有488人。翻閱花名冊(cè),竟有二代、三代同時(shí)就學(xué)于其門下。可以這樣說,中國教育史上,與書院關(guān)聯(lián)之多、用心之深、規(guī)范之全、效益之好,無人能出朱子之右。 書院與一般的官學(xué)和私學(xué)有何不同?我給文史館提交過一篇論文,以“武夷精舍”為例,以新理念、新學(xué)校、新教材和新方法闡述書院的特點(diǎn)。 新理念 “大學(xué)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朱子認(rèn)為“大學(xué)”乃“大人之學(xué)”:“明明德”指的是令人自身所具的美德顯明;而“親民”則為“新民”之義;那“至善”則指事物道理和道德的極點(diǎn)狀態(tài)。這是儒家的“三綱領(lǐng)”,所說的是顯明自身光明美德,由此推及他人,令其自我革新,以抵至善至美的境界。用現(xiàn)代人語言說,就是通過道德教育,培養(yǎng)一代“又紅又專”社會(huì)有用之才。朱子從本體論“理”的高度論述教育:性即理。人與物因其理各得其性,氣以成形。現(xiàn)實(shí)中的人性總是天命之性與氣質(zhì)之性的統(tǒng)一。前者渾厚之善,完美無缺,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普通本質(zhì);后者是天欲人性的綜合體,善惡皆有,是人的特殊本質(zhì)。一旦性為人欲蒙蔽,人性就成了人惡。但“人性可復(fù)”,一旦“去其質(zhì)之偏,物欲蔽,以復(fù)其性,以盡其倫”,人就可以為善、為賢、為圣。“學(xué)者須是革盡人欲,復(fù)盡天理,方始是學(xué)”。教育的大本和全部價(jià)值就在這里。 基于此,書院強(qiáng)調(diào)教化,追求德行的圓滿,人格的完善,心靈的高尚。錢穆說:“中國古代不言教育,而常言教化……孔門四科首德行,德本于性,則人而道天,由人文重歸自然。此乃中國文化教育一項(xiàng)重大目標(biāo)所在。”張昆將、張溪南先生在《臺(tái)灣書院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書中,對(duì)書院的性質(zhì)也如此概括:“既是立志于圣賢的人格養(yǎng)成之地,也是孕育治國平天下棟梁之才的場所,更是傳承優(yōu)良文化的堡壘。”一句話,書院德育為先,“圣賢所以教人,為學(xué)之大端”。 也基于此,書院不以科舉考試為教育目的。雖然朱子本人是從科考中脫穎而出的;雖然朱子的弟子不乏金榜題名者;雖然他日后的著作成為開科取士之制,但朱子對(duì)科考的弊端看得很清楚:“科舉之學(xué)誤人知見,壞人心術(shù),其技愈精其害愈甚”。他多次向朝廷建議改革科舉,提出由朝廷和地方聯(lián)合選拔人才。他所從事的書院教育本身就是對(duì)科舉制度的批判和修正。 新學(xué)校 “道迷前圣院,朋誤遠(yuǎn)方來”。 考亭書院這副對(duì)聯(lián)還有個(gè)故事。此聯(lián)前身為門人趙蕃為“竹林精舍”所題,“教存君子樂,朋自遠(yuǎn)方來”。朱子覺得不妥,認(rèn)為自己的道統(tǒng)還不完整明晰,恐怕會(huì)耽誤前來的學(xué)者朋友,自謙地作了調(diào)整。現(xiàn)在復(fù)建的“滄洲精舍”就是原來的“竹林精舍”,也是朱子去世44年后,宋理宗御書的“考亭書院”。大門兩邊的對(duì)聯(lián)“佩韋遵考訓(xùn),晦木謹(jǐn)師傳”也是朱子所題。意指遵守父親的遺訓(xùn),佩韋改正自己急躁的性格;不忘恩師的教導(dǎo),做一個(gè)道德內(nèi)蓄的君子。有人說前聯(lián)是“國聯(lián)”,后聯(lián)是“家聯(lián)”,當(dāng)以前聯(lián)為重。我倒認(rèn)為兩聯(lián)俱是朱子為考亭書院而撰,孰重孰輕、懸掛何處皆無礙無妨。兩聯(lián)所述之義,倒是很好地說明書院的性質(zhì)。 中國書院始于唐初,盛于宋朝,而朱子對(duì)書院制度貢獻(xiàn)是開創(chuàng)性的、全面的。岳麓書院“忠孝廉節(jié)”的道德要求;《白鹿洞書院的揭示》的教規(guī)等就是很好的例證。臺(tái)灣專家黃俊杰教授指出,中國的書院乃至同期的東亞書院學(xué)規(guī),“深深浸潤在朱子學(xué)的價(jià)值理念共同體之中。這一點(diǎn)與清代臺(tái)灣書院的碑記,顯示出強(qiáng)烈的朱子學(xué)取向……都共同反映朱子的書院教育,對(duì)于東亞地區(qū)傳統(tǒng)教育所發(fā)揮的典范作用。”朱子書院主張大體可用“傳道濟(jì)民”來概括,即賡續(xù)道統(tǒng)、培養(yǎng)經(jīng)世致用的人才。朱子是哲學(xué)意義“道統(tǒng)”的確立者。他以“危微精一”即儒家十六字“心傳”,闡述理想的“道統(tǒng)”,且將傳承排列成一個(gè)譜系:上古圣神,繼之堯、舜、禹、成湯、文武;然后孔子、顏?zhàn)印⒃印⒆铀肌⒚献樱蝗缓笾茏印ⅰ岸獭背薪忧瓴粋髦w。從中可以看出,儒家道統(tǒng)傳承自孔子之后,其重心已自覺地由君道轉(zhuǎn)移為師道,教育成了傳承的核心和重要載體。書院的種種功能都是圍繞傳道而展開。這是書院教育的重要功能,也是中華文明五千年不中斷的原因所在。 書院能夠堅(jiān)持思想學(xué)術(shù)的獨(dú)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辦學(xué)機(jī)制。雖然有些書院得到官府的支持和褒獎(jiǎng),但大多數(shù)都是民間設(shè)立的,其創(chuàng)建和運(yùn)轉(zhuǎn)主要依靠自身。本來“武夷精舍”的營建,作為時(shí)任福建安撫使的趙汝愚及志同道合者都表示要傾力相助,可朱子堅(jiān)決謝絕支持。所以他的書院經(jīng)費(fèi)更為窘迫,甚至要以私人名義向建寧府的韓元吉告貸。有位頗有身份的學(xué)生胡纮前來書院,原以為會(huì)得到只雞半鴨的接待,誰知道竟和師生共同“享受”“脫栗飯”“姜汁茄”,以致積怨甚深。“慶元黨禁”時(shí),已為太常少卿的他,落井下石,捏造了許多莫須有的事加害朱子。 新教材 “四書道理粲然……何理不可容,何事不可為”。 事實(shí)上,朱子很多著述大抵因?yàn)橹v學(xué)需要而作。他編的教材是成系統(tǒng)和配套的。既考慮到受教育者年齡大小、身份不同;又考慮到不同學(xué)子秉賦差異;也注意到教材之間的平衡與銜接;還兼顧了儒家的經(jīng)典與新近學(xué)術(shù)成果的關(guān)聯(lián)。西方學(xué)者狄百瑞將朱子的教材分為十一項(xiàng),從針對(duì)懵懂少年到皇帝達(dá)官,應(yīng)有盡有。 其中最為朱子看重的當(dāng)然是《四書章句集注》。中國古代教育經(jīng)典原來是《六經(jīng)》,漢以后失去了“樂”而為《五經(jīng)》。隨著時(shí)代發(fā)展,原來的經(jīng)典對(duì)社會(huì)發(fā)展的指導(dǎo)性、與釋老的抗衡的針對(duì)性、對(duì)學(xué)子學(xué)習(xí)的漸進(jìn)性都存在明顯的缺陷。朱子與時(shí)俱進(jìn)地以《四書》代替《五經(jīng)》。“大學(xué)”“中庸”原是《禮記》中的兩篇,而“論語”在漢代僅為小學(xué)所必修;“孟子”在此之前不具有經(jīng)的地位。朱子讓中國古文化主題更為鮮明,體系也更為系統(tǒng),也讓士子學(xué)習(xí)儒學(xué)更好地循序漸進(jìn)。朱子明確了新舊經(jīng)典的內(nèi)在邏輯順序:先《四書》后《五經(jīng)》,前者是后者的階梯。而就《四書》內(nèi)部體系而言,應(yīng)按“大學(xué)”“論語”“孟子”“中庸”的順序來學(xué)習(xí),“先讀‘大學(xué)’以定其規(guī)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fā)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微妙處”。 值得一提的是《朱子語類》。它是朱子與弟子答問語錄的匯編,其范圍廣泛,涉及眾多領(lǐng)域,展現(xiàn)了朱子宏大的理學(xué)思想體系,是“新儒學(xué)”的精華,仿佛是《論語》的新版。朱子去世后15年,弟子們就開始了搜集,直到1270年,黎靖德集大成,編成了洋洋大觀140卷本。胡適先生寫過“《朱子語類》的歷史”專文。吳堅(jiān)在“建安刊朱子語別錄長序”中說道:“朱子教人既有成書,又不能忘言者,為答問發(fā)也。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其在成書引而不發(fā)者,《語錄》所不可無也。”《朱子語類》不失為學(xué)習(xí)朱子思想的最好教輔。書中的問答方式也是書院教學(xué)的一種好方式。 新方法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沖巨艦一毛輕。 向來枉費(fèi)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這是朱子“觀書有感”詩的第二首,講的是讀書之法。第一種讀書不得法,未下苦功,學(xué)不對(duì)路,猶如水淺時(shí)推移擱淺巨艦;第二種讀書得法,痛下苦功,方法到家,如同春水漲發(fā),巨艦行駛輕如鴻毛。朱子曾說過:“道有實(shí)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錢穆先生言:“在理學(xué)家中,正式明白教人讀書,卻只有朱子一人。”有人將朱子的教學(xué)方法歸納為:對(duì)話法、講授法、引導(dǎo)法、點(diǎn)化法、時(shí)習(xí)法、示喻法和感化法。我則總結(jié)為:共性與個(gè)性的統(tǒng)一;教育學(xué)習(xí)相長;致知篤行并重;課里課外結(jié)合。 朱子在書院教育還開創(chuàng)了會(huì)講與升堂講學(xué)的制度。1167年朱子造訪湖南長沙,與張栻進(jìn)行了著名的“岳麓會(huì)講”。講論涉及主題豐富,有“太極”“中和”“仁說”等等。講論中爭論激烈,門人范伯崇回憶:“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講論氛圍熱鬧,學(xué)徒千余,輿馬之眾,至飲池立竭,一時(shí)有瀟湘洙泗之風(fēng)焉”“自此之后,岳麓之為書院,非前之岳麓矣。”朱子修復(fù)白鹿洞書院后,又邀請(qǐng)與自己學(xué)術(shù)主張不同的陸九淵前來講學(xué),并讓其打破慣例,留下提綱鐫刻于石。“武夷精舍”期間,朱子曾言:“過我精舍,講道論心,窮日繼夜。”朱子倡導(dǎo)的會(huì)講與升堂講學(xué),打破了傳統(tǒng)書院的門戶之見,為不同學(xué)派的思想提供了學(xué)術(shù)交流、爭鳴的平臺(tái)。它對(duì)探索真理、發(fā)展文化產(chǎn)生了不可估量的積極影響。 優(yōu)游山水、自然施教是朱子書院教育的另一特色。《禮記·學(xué)記》中言:“故君子之于學(xué)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朱子深以為之。在他心目中,教育是生命教育,亦即完善生命,提升生命。“天地大德曰生”。要讓學(xué)子“讀萬卷書”,更要讓他們“行萬里路”。所以在書院的選擇上,應(yīng)是山水絕佳處。議及白鹿洞書院所處地理位置時(shí),他說:“山中間曠,正學(xué)者讀書進(jìn)德之地,若領(lǐng)訪諸賢固心倡導(dǎo),不以彼己之私介于胸中,則后生有所觀法,而其敗群不率者亦且革心矣。”辦學(xué)“武夷精舍”,更是把整座武夷山作為教學(xué)空間,經(jīng)常帶領(lǐng)學(xué)生游歷靈山秀水,從中領(lǐng)略理學(xué)的深刻哲理。門人葉賀孫曾說:“及無事領(lǐng)諸生游賞,則徘徊顧瞻,緩步微吟。”膾炙人口,流傳百世的《九曲棹歌》就是這樣寫就的。 “興發(fā)千山里,詩成一笑中”。此刻,朱子吟誦之聲又回響耳邊: 五曲山高云氣深,長時(shí)煙雨暗平林。 林間有客無人識(shí),欸乃聲中萬古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