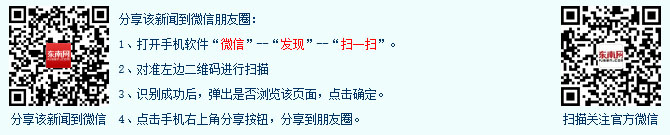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語類》卷一三) 人的心胸要開闊宏大,表現在接人待物上,如果在意分彼此、講厚薄,則是心胸狹窄的表現。要像君子那樣胸懷天下,容得下天下之人、天下之事,這樣,你人生的格局才會寬闊。試想,如果讓人人都能發揮自己的才情,那是一件多么快活的事情! 于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于內顧偏聽之私;于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里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文集》卷二九《與留丞相書》) 處理各種事情,肯定還是否定,要以公正為判斷的標準,不能有照顧親友、偏聽偏信的私心;面對各種議論,聽從還是反對,要開誠布公,不能耍陽奉陰違的詭計。這樣你就能增進自己的德行與功業,光明磊落,不論中外遠近的人都對你心悅誠服。 大抵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行舍藏之間,隨所遇以安之。和靜先生云:“如霽則行,如潦則休。”此言有味也。(《文集》卷三九《答魏元履》) 孔子夸獎他的學生顏回,說他吃的是粗茶淡飯,住的是陋室寒屋,可是卻“不改其樂”。所以孔子給顏回點了一個大大的贊,說:“賢哉,回也!”對此,朱子解釋說:“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 那么,為什么顏回能不改其樂呢?朱子引用程頤的話說,顏子不是因為艱苦的生活而快樂,而是沒有因為生活的艱難而改變自己內心所堅守的快樂。于是,這又引出了一個更深的問題: 什么是顏回所堅守的快樂呢? 程頤說,粗茶淡飯和陋室寒屋肯定沒有可樂之處,“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朱子說,程頤在這里賣了個關子:“引而不發”——要你自己去思考、琢磨。從此,顏回之樂,就成了中國哲學史上一個被反復討論的課題。 朱子說“大抵人當有以自樂”,是給我們換了一個思路來看這個問題,他拋開顏子之樂的具體內容不談,而是強調,一個人總應該有一處自我愉悅的精神港灣,這樣他才能做到像孔子所說的“我被任用了,就施展才干;不被任用,就退隱民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表現得自如灑脫。 北宋有一位叫尹焞的學者說:“天晴了就出門,下雨了就在家休息。”這句話的意思真是值得玩味。朱子為什么欣賞這句話呢?原來這句話就是孔子強調的另一種精神——不主觀(毋意)、不武斷(毋必)、不固執(毋固)、不自我(毋我),也就是隨遇而安。 心有喜、怒、憂、樂則不得其正,非謂全欲無此,此乃情之所不能無。但發而中節,則是;發不中節,則有偏而不得其正矣。(《語類》卷一六) 好、樂、憂、懼四者,人之所不能無也,但要所好、所樂皆中理。合當喜,不得不喜;合當怒,不得不怒。(《語類》卷一六) 四者人所不能無也,但不可為所動。若順應將去,何“不得其正”之有?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移于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語類》卷一六) 人心如果被喜、怒、哀、樂所左右,那么人的正確的情緒、情感、理智就會失控。這并不是說人不可以有這些感情,這些感情是人所不能沒有的。關鍵是,當這些感情發生的時候,是不是符合節度,不走偏(中節)。“中節”了,就是正確的;不“中節”,就是偏差的,心就失去正確、平常的心態(不得其正)了。 好、樂、憂、懼這四種情感,是人所不能沒有的。但是,要做到所好、所樂都符合“理”。該高興的,就高興;該發怒的,不能不怒。 喜、怒、哀、樂這四樣東西,是人所不能沒有的。但是人不能被這四樣東西牽著鼻子走。如果能做到不為所動,那怎么可能“不得其正”呢?比如顏淵講“不遷怒”,他是怒在物上、事上,他從來沒有被自己的血氣所動而把怒氣遷移到別人身上。這樣的怒,怎么可能“心有不正”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