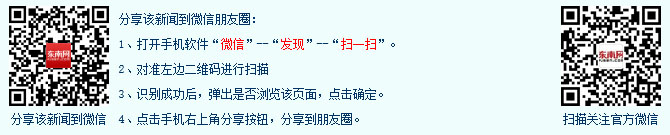|
二 朱熹生活在宋朝,恰是“重文治”“輕武功”的時代,統治階級由“武功”轉向“文治”。宋太宗于太平興國七年(982)明確提出:“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于是“興文教,抑武事”,北宋進入教育的繁盛時期。但是由于北方金族入侵中原,1126年北宋首都開封被攻陷,俘虜了宋徽宗和宋欽宗,宣告了北宋王朝的滅亡,以趙構為首的宋朝王室于1127年在臨安建立起南宋王朝。山河破裂,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思想斗爭,各種矛盾極為激烈和復雜。西漢之際佛教傳入中國,中國本土宗教道教也已產生,于是形成了儒釋道三教鼎力的局面。由于朝廷尊孔崇儒又提倡佛老,而漢代董仲舒的天命論儒學又不適用于國家指導思想,于是儒家學說走向式微,以致于自命孟子之后的韓愈大聲疾呼,“道斷”。北宋五子和朱熹們全力應對道德日下、外來文化和理論傳承的挑戰,力圖恢復和確立國家的主體意識,重建社會理想和人格境界。而作為宋朝的教育重要形式的官辦學校,大致分為:國子學和太學,具有大學性質;武學、律學、書學、算學、道學和醫學,屬專科性質;宗學、諸王宮學、內小學和國立小學,屬貴胄性質;還有群雍、廣文館、四門學等,屬特殊性質。地方學校分為洲學和縣學。各級官學入學條件較嚴,招生人數也有限定,主要是服務官僚階層的子弟,其終極目標就是為科舉考試服務。這樣培養的人才離宋太祖趙匡胤所確立的“文德致治”的要求相去甚遠,培養出來的士人、儒者、官員、軍人浸淫著升官發財、貪圖享樂的思想,真的是“文官貪財,武官怕死”,以致金軍鐵蹄所及,如入無人之境,大宋王朝不是“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而是“安不下一張行軍床”。朱熹和大批知識分子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當作己任,模仿孔孟行為,撰寫奏疏,向朝廷和地方官府提出救國復興的積極建議。然而道不行,他們轉而從事思想理論研究和文化教育,為國家鑄造新的精神武器和新的人才。朱熹大力鼎故革新,采用新的理念、新的學校、新的教材、新的方法,不遺余力地培養天下英才。 (一)新理念 朱熹直承孔孟,把孟子關于教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為宗旨,闡釋說“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眾,而天下后世將無不被其澤矣。”一句話,教育的宗旨是使人向善,不僅是個體人格的完善,還要使社會性集體人格完善。《大學》開篇指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即儒家的“三綱領”。朱熹注釋“親民”解為“新民”,也就是要求社會精英們在自己擁有高尚德行后,還要引導全社會明德善行,不斷追求至善境界,造就一代又一大新的社會有用人才。朱子規劃了圣賢君子培養的“路線圖”: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儒家所謂的“八條目”。在這個發展鏈條中,“修身”是“內圣外王”的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也是教育的全部價值所在。其哲學依據可從朱熹的理氣論和人性論上進行說明。“理”是朱熹哲學的最高范疇。他把仁義禮智等道德原則統一于天理,“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這樣,他就在理一元論的前提下,構建了道德倫理的形而上學,使道德教育具有了本體論依據。由此推出“性即理”,人與物因其理各得其性。現實中的人性總是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的統一,前者是天理,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普遍本質,后者則是人的特殊本質,是天理和人欲的綜合體。但“性可復”,性發而情,“心統性情”,“只是這個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道心是善,人心“可為善,可為不善”,只要主敬涵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變化氣質,就能人心變道心,止于至善,成為圣賢君子,成就天下大業。 (二)新學校 朱熹的教學活動既重官辦學校,更與私立書院關系密切。史志記載,與他有直接關系的書院多達67所。其中親手創建的4所、修復的3所、讀書的6所、講學的20所、撰記題詩7所、題詞題額的6所。鐘情書院教育,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朱熹可謂第一人。中國書院始于唐初,盛于宋代。如果說唐代的書院只是作為官學的補充,那么朱熹的教育實踐則賦予書院全新的內容,鄧洪波教授撰寫的《中國書院史》指出,書院規制在北宋就已經形成,但書院教育制度的確立卻是朱熹完成的。朱熹將書院規制擴展為研究、講學、藏書、刻書、祭祀、學問六大事業;朱熹制定了書院的學規,即《白鹿洞書院揭示》,列出了“圣賢所以與人人為學之大端”,分為五教之目,為學之序,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揭物之要,朱熹還編寫刊印了系列教材。 由于書院大多由民間設立,國家雖有支持和褒獎,但其經濟和辦學思想是獨立的,主要由私人管理和組織教學,書院就大大有別于官學和一般私學,書院教育主要是完善個人品德和增進學識,培養“傳道濟民”的人才。書院有著自身的學術師承。書院不是單純的師授生學的被動學習,而是以學生讀書思考為主,輔之以碩儒會講、師生討論、學生切磋等教學形式,十分注重“對話”學風的發揚,追求極大的自由精神。書院有教育更有教化,強調德行的圓滿,人格的完善,心靈的滿足。國學大師錢穆說過:“中國古代不言教育,而常言教化……孔門四科首德行,德本于性,則人而道天,由人文重歸自然。此乃中國文化教育一項重大目標所在。”書院不同于官學的最大特點就是不以科舉考試為目的,它是對科舉考試的修正和批判,也是對教育宗旨的正本清源。雖然通過書院教育不乏金榜題名者,雖然朱熹本人也是通過科舉考試脫穎而出的,且他的著作后來作為開科取士之制,但他卻是科舉考試的堅決反對者。朱熹在《信洲洲學大成殿記》文中說,“士子習熟見聞,因仍淺陋,知有科舉而不知學問。”在《答騰德章》信中說,“科舉之學誤人知見,壞人心術,且技愈精,其害來愈甚。”朱熹極力主張對科舉考試進行改革,既不同意當時宰相趙汝愚的“三舍法”,也不贊成其他人提出的“溫補法”。提出自己的方案,要求州縣共同承擔選拔人才的責任,要求以德為先培養人才,選拔敢于承擔大任而有實學者。朱熹對科舉考試的批判是嚴厲的,甚至直斥士子“釣聲名,干利祿”,“至于后世,學校之設雖成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于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這就是朱熹為什么熱衷于興辦完全不同于官學教育路線的書院的原因。 |